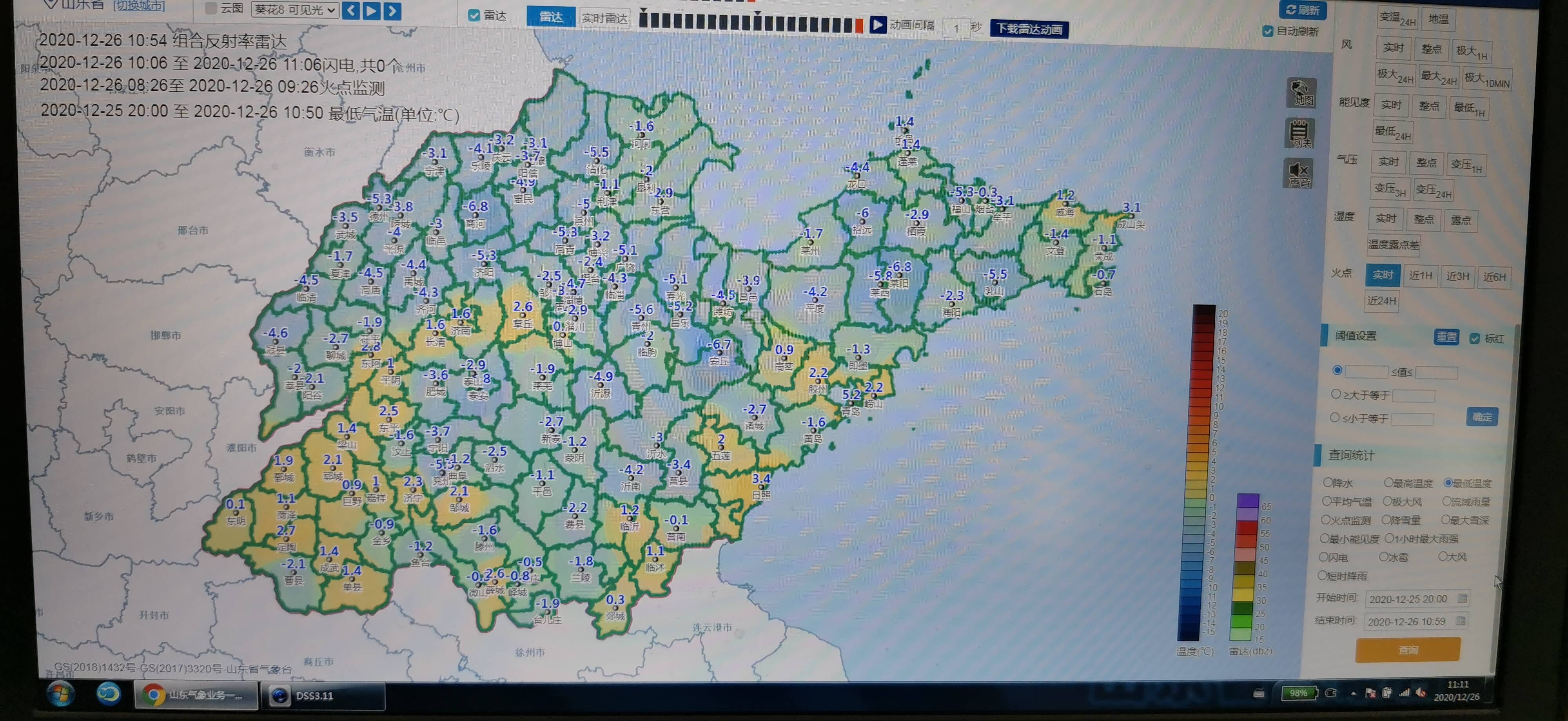“中華蟋蟀第一縣”為啥是山東省寧津縣
來源:大眾日報
2020-12-27 09:41:12
原標題:“中華蟋蟀第一縣”為啥是山東省寧津縣
來源:大眾日報
“兒時,曾記得,呼燈灌穴,斂步隨音。任滿身花影,猶自追尋。”宋詞《滿庭芳·促織兒》中所述場景,曾出現在時下很多人的童年記憶里。促織,即蟋蟀,又名蛐蛐、秋蟲等,常常在北方的秋夜里,鳴響整個村莊。而寧津縣的蟋蟀叫聲格外響亮,且體健力足、牙齒尖利、剽悍好斗,在斗蟋“江湖”上歷來小有名氣,也因此衍生出蟋蟀陶制作等諸多相關行當,全縣形成80多個蟋蟀專業村,養蟋蟀、做陶器、賣器具,相關從業人員2萬余人。
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寧津挖掘蟋蟀文化,出版了蟋蟀志,發展為蟋蟀罐生產基地縣,建起蟋蟀文化博物館,連年舉辦蟋蟀文化節、博覽會,遂有了“中華蟋蟀第一縣”之稱。好水土養出好“秋蟲”
蟋蟀主題的盛會,自然要在秋天舉辦。今年9月底,第八屆中國(寧津)蟋蟀文化博覽會開幕,來自天南海北的蟋蟀愛好者蜂擁而至,寧津的街頭巷尾,到處是賣蟋蟀、選蟋蟀、買蟋蟀的人,熙熙攘攘,東北高聲、吳儂軟語、齊魯腔調不絕于耳。此等熱鬧每年都會持續一月有余,博覽會只是其中一個小節點而已。
博覽會上最為忙碌的人當數寧津縣文化協會會長李海濤,他給各地趕來的媒體記者和首次參加博覽會的游客介紹著寧津的蟋蟀。“蟋蟀文化以南北劃分,南方以江、浙、滬為代表,北方以京、津、冀、魯為標志。而眾口皆碑的極品蟋蟀產地,首推齊魯,并以寧津、寧陽兩地為最。”他不掩自豪神色,“如果說山東是蟋蟀王冠,寧津就是王冠上的明珠。”
寧津為何盛產極品蟋蟀?這與寧津的自然稟賦密不可分。寧津土質系黃河沖積而成,澄漿膠泥,板結黏韌,燥濕合宜,酸堿適度,并且其中含有大量鈣、鐵、錳、鹽離子,蟋蟀在其中發育成長,自然增強了骨密度值,其頭顱堅硬、牙齒鋒利、腳力異常蓋源于此。
然而地處黃河沖積平原之地甚多,為何寧津獨享產蟋盛名?有人繼續探問下去,李海濤就推薦其去看中國科學院博士生導師吳繼傳教授所著《中國寧津蟋蟀志》,吳繼傳不僅是中國科學院中國昆蟲研究所所長、昆蟲學家,而且身兼中華蟋蟀研究協會會長,被蟋蟀界尊為“蟲圣”。先生著述頗多,僅蟋蟀研究專著就有《中國斗蟋》《中國巨蟋油葫蘆譜》《中華鳴蟲譜》《中國蟋蟀圖畫譜》等大部頭著作。作為蟋蟀學研究的學術權威,為寧津蟋蟀出版專著,足見寧津蟋蟀確實了得。
《中國寧津蟋蟀志》為全國首部蟋蟀志,書中解釋,除土壤條件外,寧津特有的地理位置、生態條件,以及相應的氣候因素,加之常年籽粒品種特性的遺傳,使得所產蟋蟀兼具南北蟲的優點。在格斗時咬法多樣全面,既有南蟲的爆發力,又有北蟲的體質與咬死不走的頑強斗性。
寧津出產極品蟋蟀的原因,在當地還有這樣一個傳說,頗為有趣。北宋年間,徽欽二帝疏于國事,在宮中建臺斗蟋,樂此不疲。徽帝的皇后是寧津所在地德州刺史王藻之女王敏。王敏知書達禮,深明大義,多次勸說徽帝節制玩心,竭智謀國,卻不見效,反被冷落疏遠,不久抑郁而亡,年僅25歲。死后,她變身一只烏頭金翅大蟋蟀,來到徽帝身邊,終日在其耳邊啼鳴:“夫君醒來!夫君醒來!”
東京汴梁被破后,徽欽二帝被金軍劫持,連同宮中之物,一并驅往幽州。當車行至鬲津河畔臨津縣即今寧津縣時,天氣突變,烏云翻滾,一聲霹靂,車裂盆碎,烏頭金翅大蟋蟀一聲鳴叫,群蟲振翅齊聲,沒入草野。蟋罐“化身”藝術品
今年九月,劉秀芬和張建強夫妻載著蟋蟀罐從寧津劉營伍鄉驅車趕到第八屆蟋蟀文化博覽會,他們的“劉記丫頭”蟋蟀罐是山東省非物質文化遺產,近幾年縣里舉辦的蟋蟀文化節和博覽會都未曾缺席。
玩蟲一秋,玩罐一世。蟋蟀罐、蟈蟈葫蘆,以及過籠、水槽、探筒等蟲具,不僅是玩蟲的必備之物,也是不少蟋蟀愛好者的收藏之物。因為玩蟋蟀得有好器具,若隨便用一個家什,比如鐵筒、塑料筒裝蟋蟀,趣味就寡淡了。而寧津地下的古黃河澄泥,細膩、純凈,漳衛新河劉營伍鄉段的泥土含膠量又恰在60%到80%之間,這正是制作蟋蟀罐的最佳區間膠度。所以孕育了“丫頭罐”、張華新蟋蟀罐、樸樹堂蟋蟀罐、張吉峰過籠等享譽全國的陶器品牌。
“丫頭”是劉秀芬的乳名,為“劉記丫頭”蟋蟀罐的傳承人,因其制作的罐子難以模仿,遂有了一個專屬稱呼——“丫頭罐”。劉秀芬的表姑父谷德恩是蟋蟀罐制作高手,她初中畢業后便跟隨表姑父學習蟋蟀罐制作,頗具靈氣。丈夫張建強祖上便以制陶為生,米缸、米罐等生活器具為主,手藝代代傳承下來,傳統尚存。小兩口結婚后,正趕上寧津縣舉辦蟋蟀節,帶動得蟋蟀罐這一產業紅紅火火,他們就商量,恢復自家的制陶作坊,在繼承傳統制作技術的基礎上,結合制陶工藝,生產蟋蟀罐。
十余年過去,二人制罐手藝已甚為精湛,丫頭負責定型和壓光,張建強則依靠足夠力量和溫度把控,進行揉泥和燒制,唯有如此,方有“劉記丫頭”蟋蟀罐的精致。張建強的名頭似乎并不如妻子響亮,但事實上,他的制坯和燒制手藝,也是他人望塵莫及的。曾有南方玩家到此買罐,觀之制坯速度和質量后驚嘆,“單這手法在我們當地便能月入近萬元。”
記者隨二人到其家中,院中、屋內,四處皆是蟋蟀罐,從澄泥顏色上,就有朱砂紅、鱔魚黃、蟹殼青、檀香紫、墨玉黑等多種顏色。“蟋蟀罐有南北之分,也就是蟲客們所說的‘南盆北罐’。”劉秀芬說,南盆腔壁薄而北罐腔壁厚,乃為氣候所致。北罐較為厚重,養蟲隔音好,溫濕度波動慢,南盆相對輕巧,透氣性稍好。“最初此類器皿皆被稱為‘盆’,隨著民間蟋蟀文化的日漸深厚,不知何時,北方器物開始稱為‘罐’,而南方依然稱為‘盆’,雖然沒有嚴格界定,北方也常常盆、罐混稱,但大致上約定俗成,沿襲至今。”
也因技藝精湛,夫妻二人手中訂單,已排至明年10月。她告訴記者,整個劉營伍鄉燒蟋蟀罐的作坊有30余家,小泥罐遠銷全國各地,儼然已是北罐的主要出處之一。丫頭家在其中并非產量最多者,卻是產值最大者,其中差距便在于手藝——“丫頭親手制作”。有北京蟋蟀玩家評論“劉記丫頭”蟋蟀罐:既有中國北罐的渾厚大氣,又有中國南罐的細膩秀美。這使其成為蟋蟀玩家收藏和民間饋贈的珍品,張建強說,日后有意建廠,也會選在鄉里,挖河泥,捉蟋蟀,罐子也就做得更有意趣。 “青紗帳”里尋“將軍”
在蟋蟀博覽會之前半月,丫頭家的農家院里便熱鬧起來,南腔北調的蟋蟀玩家來自全國各地,北京和天津等地居多,他們往往睡至晌午,吃飯、喝茶,待入夜后,戴上頭燈隨張建強摸進黑漆漆的玉米地。此等生活往往會延續十余天,不辭辛苦一為得兩尊丫頭親手做的蟋蟀罐,二為在寧津的膠泥地里捉幾員蟋蟀“猛將”。
寧津縣的捉蟲能手大有人在,有人稱之為“蟋蟀獵人”。他們或如張建強一般,為外地的蟋蟀愛好者做“向導”,或自捉自賣。所以夜幕降臨時,寧津縣各鄉鎮的玉米地里,一道道頭燈光線搖曳,“捉蟲大軍”來回穿梭,在“青紗帳”里尋找至后半夜。在頭燈的照射下,蟋蟀變得謹小慎微,張建強不斷地扣下網抄,他將捉來的蟋蟀裝入特制的竹筒里。
蟋蟀客們還喜歡去蟋蟀市場,寧津現已形成大型蟋蟀交易市場6處,分別位于縣城車站步行街、縣城東關、孟集、尤集、柴胡店和保店鐵莊。有的玩家每年都會來寧津,久而久之也就有了相熟的本地“蟋蟀獵人”,到了市場上,往往直奔目標攤位。
今年35歲的陳華子是“蟋蟀獵人”中的佼佼者,時常出現在柴胡店鎮尤集市場上,其父陳方彬是山東省非物質文化遺產——斗蟋項目傳承人,是個“蟋蟀通”,捉蟋蟀、收蟋蟀、賣蟋蟀已有50多年,在業內小有名氣。在蟋蟀博覽會上,父子二人一出現,蟋蟀玩家、蟋蟀賣家便都圍了上來。兩個小時后,倆人以1—200元不等的價格收購了大批蟋蟀。接下來,他們要將捉來的以及收來的蟋蟀重新打包,三五個小時后,陳華子將帶著它們出現在天津的蟋蟀市場上。
“寧津蟋蟀中最出名的是大青翅子,在蟋蟀中為異形福相,是蟋蟀中的佼佼者。”陳華子說,斗蟋蟀是中國民間博戲之一,僅有雄性參與,它們為保衛自己的領地或爭奪配偶權而相互撕咬。“二蟲鏖戰,戰敗一方或是逃之夭夭或是退出爭斗,倒是鮮有‘戰死沙場’的情況。”
寧津迄今已舉辦八屆“斗蟋大賽”,今年因疫情,縮小了規模,但還是有來自全國各地的十幾個代表隊前來參加。在紅布鋪就的擂臺上,透明的蟋蟀盆內有兩只青頭大蟋蟀,兩雄相遇,一場激戰就開始了,通過大屏幕,兩員“大將”的爭斗細節清晰可見:首先猛烈振翅鳴叫,一是給自己加油鼓勁,二是要滅滅對手的威風,然后才齜牙咧嘴地開始決斗。頭頂,腳踢,卷動著長長的觸須,不停地旋轉身體,尋找有利位置,勇敢撲殺。幾個回合之后,弱者敗下陣去,勝者仰頭挺胸,趾高氣昂,向主人邀功請賞,現場頓時掌聲響起,獻給那勝者的勇猛,也獻給敗者的無畏。
然而,不管是歷史上,還是當代,人們對斗蟋蟀的看法不一。斗蟋蟀始于唐代,盛行于宋代,傳至清代,每日里斗雞走馬的八旗子弟自然更加熱衷此事,從清代蒲松齡名篇《促織》中便可看出當時斗蟋蟀風俗之盛,以至于有人因一只好蟋蟀而得到皇帝嘉獎,雞犬升天。
“蟋蟀雖是玩物,但其本身也是具備文化韻味的。”李海濤說,古人將玩蟋蟀分為三種境界:其一玩物喪志,也就是專注于玩蟋蟀以致無心他事,志氣消磨,其中典型便是南宋的蟋蟀宰相賈似道,因玩蟋蟀誤國而留下罵名;其二則玩物娛賭,意為玩蟋蟀只是為了娛樂或小賭怡情;而其三便是托物寓情,也就是文人雅士賞玩蟋蟀,同時吟詩作賦,托物抒情。他認為,“時至當下,斗蟋已不是少數人的賭博手段,它和釣魚、養鳥、種花一樣,成為人們彼此交往、陶冶性情的文化生活,或可稱之為具有東方特色的‘蟋蟀文化’。”
正如本屆斗蟋大賽上北京選手吳子介所言,“結果不重要,斗的是一份童趣和情懷。”(張雙雙 孫久生)(完)

想爆料?請登錄《陽光連線》( https://minsheng.iqilu.com/)、撥打新聞熱線0531-66661234或96678,或登錄齊魯網官方微博(@齊魯網)提供新聞線索。齊魯網廣告熱線0531-81695052,誠邀合作伙伴。

王帆:你若得溫暖,國家便溫暖,我是孩子的“國家監護人”
- [詳細]
- 齊魯網 2020-12-27
沈陽公布3例確診患者關聯病例行動軌跡:一人為護士
- 12月26日,沈陽市新增3例新冠肺炎境外輸入病例尹某某的關聯病例,現均已轉入定點醫療機構隔離治療,病情穩定。(一)徐某某,女,35歲,中國...[詳細]
- 人民日報客戶端 2020-12-27
北京城市副中心三大建筑長啥樣?
- 新華社北京12月27日電(記者關桂峰)形如“赤印”的圖書館,“帆船”模樣的博物館,“糧倉”構造的劇院,在北京城市副中心,正在建設的三大...[詳細]
- 新華網 2020-12-27
沈陽3例確診病例行程軌跡公布!
- 12月26日,沈陽市新增3例新冠肺炎境外輸入病例尹某某的關聯病例,現均已轉入定點醫療機構隔離治療,病情穩定。徐某某,女,35歲,中國籍,...[詳細]
- 遼寧日報 2020-12-27
中央統戰部定點扶貧貴州望謨縣:幫扶全方位 黔貨走出山
- 中新網北京12月27日電中央統戰部作為貴州省望謨縣的定點扶貧單位,截至目前,已統籌本領域實施幫扶項目61個,投入資金774.73萬元(人民幣,...[詳細]
- 中國新聞網 2020-12-27
廣東高院對黃耀宏等29人涉黑案二審宣判 維持原判
- 中新網12月27日電據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官方微信消息,近日,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依法對黃耀宏等29人涉黑案及刑事附帶民事訴訟案二審宣判,裁...[詳細]
- 中國新聞網 2020-12-27
2020年1—11月全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同比增長2.4%
- 中新網12月27日電據國家統計局網站消息,1—11月份,全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實現利潤總額57445.0億元,同比增長2.4%,增速比1—10月份提高1.7...[詳細]
- 中國新聞網 2020-12-27
北京西城啟動冷鏈、餐飲等關聯從業者每周循環核酸檢測
- 中新網北京12月27日電為貫徹落實北京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小組會議精神,持續加強冬春季節疫情防控工作,嚴防元旦、春節假期人員流動、聚集...[詳細]
- 中國新聞網 2020-12-27
國家統計局:工業企業利潤持續穩定恢復
- 中新網12月27日電據國家統計局網站消息,國家統計局工業司高級統計師朱虹解讀工業企業利潤數據時指出,11月份,各地區各部門繼續扎實做好“...[詳細]
- 中國新聞網 2020-12-27
習近平時間 | 提高創新能力 解決“卡脖子”問題
- 習近平時間 | 提高創新能力 解決“卡脖子”問題[詳細]
- 新華社 2020-12-27
濟南歷城蘆南村:一個山村的“脫貧密碼”
- 在山東省濟南市歷城區,蘆南村是一個地理位置偏遠的貧困山村,在它的“脫貧密碼”里,村莊變社區、農業變產業、農民變股民。村里大多數人夏...[詳細]
- 大眾日報 2020-12-27
泉城濟南水務成績單:日供水能力將新增50萬方
- 在全省率先消除劣Ⅴ類水體趵突泉等重點泉群17周年持續噴涌城區供水管線達4000余公里,服務人口約500萬人農村自來水普及率超98%,225萬人實...[詳細]
- 濟南日報 2020-12-27
國內首個鯤鵬警務云在廣西欽州發布
- 華為鯤鵬警務云上線儀式。欽州市委宣傳部提供。華為廣西政企業務總經理沈秀松表示,華為將自身5G、人工智能、云計算、鯤鵬、大數據、物聯網...[詳細]
- 中國新聞網 2020-12-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