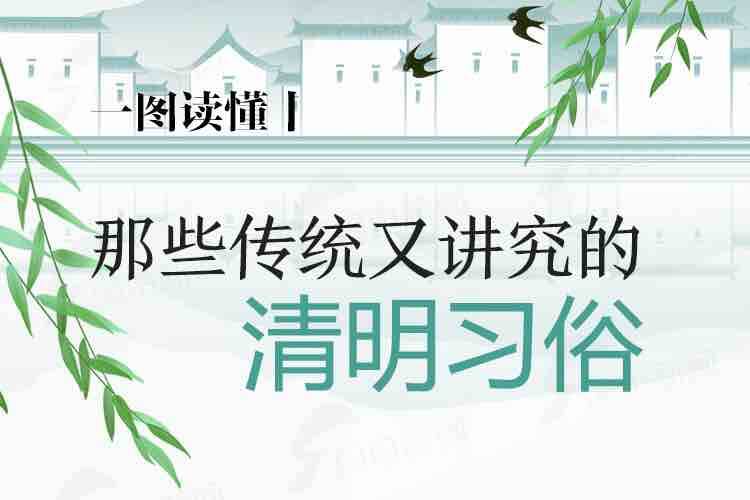蹲點深一度丨讓安寧“療護”更多生命溫柔謝幕
來源:大眾報業·大眾日報客戶端
2021-04-06 06:04:04
原標題:蹲點深一度丨讓安寧“療護”更多生命溫柔謝幕
來源:大眾報業·大眾日報客戶端
◎生命的最后時刻,“有創救治”還是“安寧療護”?
母親去世后,一位病人家屬陷入長時間的自責與反思:將母親送進ICU是不是錯了?讓母親遭這么多罪是不是錯了?最后的幾天里母親沒有享受到任何生命的權力,生命的意義何在?當然,也有家屬與病人選擇“安寧療護”,在生命的最后時刻,與家人溫暖告別。
◎安寧療護中心里的場景,是怎樣的?
在聊城市東昌府區中醫院安寧療護中心,20多張病床已經滿員,幾乎都是疾病終末期患者,沒有極端的搶救,每天都有人在這里安詳離開。在這個安寧療護中心,有的患者見證了女兒的婚禮、有的患者第一次說出了愛、有的患者把最后一句感謝留給了醫生……
◎選擇“安寧療護”的人,為何不多?
“安寧療護”的理念不被人所熟知、認可,家人更傾向于對臨終人的竭力搶救。病人生命瀕危之時,常常會被送進重癥監護室。多數家屬在面臨“救”與“不救”的選擇時,還是會毫無猶豫地選擇“救”。一名病人家屬說,拼盡全力救治家人,一方面是為了讓自己有個心理安慰,一方面是害怕家人的指責。
◎“安寧療護”發展困局,如何破解?
山東在1998年便開始開展安寧療護工作,但20多年過去,發展速度、規模、質量已落后于上海、廣東等地。做好此項工作,相應的政策制度配套支撐是第一位的,其次還需好經驗的借鑒傳播,需要更加廣泛的群眾接受度和參與度,需要全社會多個系統的支持配合。
(視頻素材:濟南市歷下區啟明星生命關愛中心)
□本報記者 常青
當生命走到盡頭,當所有的醫療手段都已經無力回天,除了痛苦離去,患者能否得到更多的醫療服務與人文關懷,與這個世界溫暖告別?
近幾年,我省多家醫療機構啟動了安寧療護試點,對終末期疾病患者進行治療。記者通過調查發現,安寧療護試點在我省取得一定成效,但也面臨著難以廣泛普及的困境。
什么是安寧療護
見到曲亞敏時,她的母親已經去世一年多了,但母親臨終前的樣子卻時常浮現在她的腦海里。
“不論如何,一定要讓她活著。”曲亞敏得知母親病危后,遠在四川工作的她,趕忙奔向機場,用最快速度飛回濟南。起飛前,她接到弟弟的電話,是否要把母親送進ICU,家里人要讓她這個大姐做個決定。
“有過一絲猶豫,但只要能延長她的生命,讓我做什么、花多少錢都在所不惜。”掛了電話,曲亞敏隱約感覺到母親的生命可能要走到盡頭了,患癌這段時間以來,住院、化療、吃藥,她清楚母親很痛苦,家里人也很難熬,但只要人還在,這就還是一個家,她就還有媽媽。
飛機落地,曲亞敏用最快的速度奔向醫院,沖進ICU,她被眼前的場景驚呆了。母親全身插滿了管子,手腳已被綁住,情緒激動、呼吸不暢、滿頭大汗,極力想要掙脫。
隨后的幾天,母親病情不斷惡化,在ICU里接受了一切能延長生命的搶救。母親去世后,曲亞敏陷入了很長時間的自責與反思:將母親送進ICU是不是錯了?讓母親遭這么多罪是不是錯了?最后的幾天里母親沒有享受到任何生命的權利,生命的意義何在?“只是證明我很愛很愛她嗎?”
與曲亞敏不同,面對與至親的告別,張梁覺得自己做了正確的決定,沒有一絲遺憾。
“當時就是覺得不舒服,一查發現是肺癌晚期,醫生說存活期只有一年左右。”面對父親的突然患病,作為獨生子的張梁陷入了兩難,是誠實告知還是隱瞞。從醫生辦公室走回病房的那幾步,無比艱難。
山東省立醫院腫瘤科的陳健鵬作為主治醫師,看出了這個年輕人的崩潰,決定給予這個家庭安寧療護服務。在他的建議幫助下,張梁向父親坦白了病情,出乎意料的是,父親比他想的要平靜得多,也逐漸接受了自己患癌的事實。
隨后的一年里,沒有了無休止的撒謊哄騙,父子倆反而有了更多心貼心的交流。張梁在上海工作十幾年來,父親沒向他提過要求,直到患病后的某一天,父親主動說趁著身體還能動,想去看一看上海。
隨后的日子里,張梁將父親接到上海和自己住了一段時間,第一次坐高鐵、第一次去上海、第一次去看看兒子生活的地方,第一次全家一起在上海過了一個年……在有限的生命里,張梁竭盡所能完成父親的心愿,了卻他心里的牽掛。他說這個過程無比心安。
在父親生命的最后一周,張梁在陳健鵬醫生的建議下,決定不給父親做過度治療來延長生命,相反他在有效的時間里對父親進行了一次告白,在那次談話里,他與父親解開了很多心結,向父親表達了感謝,與父親溫暖告別。“他走時很平靜也很安詳,我知道他沒有遺憾了,我也是。”
在控制身體疼痛癥狀的同時,關注患者的內心感受,呵護患者全生命周期的最后一環,幫助患者舒適而有尊嚴地走完人生最后一段旅程,幫助其家屬應對患者疾病過程的困難與哀傷問題,這是安寧療護的定義。
作為多年為患者提供安寧療護服務的腫瘤科醫生,陳健鵬說,安寧療護不是不用藥、不治療,而是相對ICU等的“有創救治”,更多的是想辦法為疾病終末期或臨終前人員緩解生理、心理上的痛楚,盡可能維護生命質量,幫助患者舒適、安詳、有尊嚴地走完人生的最后階段。
安寧療護機構的一個樣本
2019年,我省聊城、淄博、菏澤3市被納入國家級安寧療護試點市,啟動了安寧療護工作。3月上旬,記者選擇起步較早的聊城市東昌府區中醫院蹲點采訪。
安寧療護中心位于這所二級甲等醫院的11樓,電梯門打開,一幅希望之樹的壁畫映入眼簾,樹葉嫩綠,喜鵲報春,讓人不覺得這是每天都有人離去的病區。
房區內很安靜,主治醫生宋玉軍一天內5次到1號病房主動查房,盡管患者已經沒有能力再向她提出任何需求。
“預計生存期還有一周左右。”醫生辦公室里,宋玉軍告訴記者,患者李大娘是位70歲左右的卵巢癌晚期患者,2個月前入院,在過去2年里,她的家人帶她輾轉過9家醫院,住了9次院,當生命走到盡頭,家人只想讓她走得舒服一點,于是選擇了安寧療護。
腹痛、惡心、嘔吐,吃不下食物,這是李大娘入院后最大的生理反應,對癥下藥但又不過度治療,宋玉軍開了一些鎮痛藥物同時輔助中醫音樂療法,有效緩解了李大娘的癥狀。然而通過多次的心理疏導與留心觀察,宋玉軍發現了問題。
“她是個內向、好強的人。”因為不愿意表達,患者習慣性地選擇忍痛,因為害怕疼痛而選擇不進食。隨后的幾天,宋玉軍更加頻繁地來找李大娘聊天,從簡單的吃什么、怎么吃開始,拉家常,做些簡單的科普,勸慰患者吃點東西,李大娘覺得醫生說的有點道理,便開始照做,也逐漸打開了心門,開始信任這個“好閨女”。
安寧療護面向的是患者,也是家屬。李大娘的兩個女兒很孝順,沒日沒夜地照顧老母親,一邊承受著身體的疲憊,一邊忍受著母親隨時會離開的痛苦。交流溝通,勸慰紓解,宋玉軍同樣在竭盡所能地關懷家屬。在病區里有一間談心室,宋玉軍經常在這里安慰兩個女兒,這天,她交待了李大娘的情況后,同時詢問家屬是否需要殯葬服務,她可以幫忙對接。談心室里掛了這樣一句話:一切都會過去的。
記者采訪這幾天,李大娘總是昏沉沉地睡著,但宋玉軍卻更加頻繁地來查房,她覺得老人似乎還有沒放下的事。“通過觀察她和親人的互動,我覺得她還有想見的人。”從小帶大的外孫因為當兵一直沒能回來,每次視頻電話,李大娘總是特別高興,宋玉軍覺得那個未了的牽掛應該是這個孩子。
告知親屬后,外孫請假從部隊趕回。“即便已經意識不清,身體極度虛弱,但我知道她的心愿了了。”宋玉軍說。
聊城市東昌府區中醫院安寧療護中心,一共有6名醫生和8名護士,20多張病床已經滿員,幾乎都是疾病終末期患者,沒有極端的搶救,每天都有人在這里安詳離開。科主任高繼峰是這個團隊的主心骨,2016年起便開始在病房推行安寧療護工作,他希望通過團隊的努力,讓更多人好好地“走”。
在高繼峰的辦公桌上,放著一打生命關懷支持系統服務記錄表,里面記錄了患者的基本情況以及每次與患者談心的總結與評價,包括對死亡的觀念與認知、重要成就、重大挫折、放不下的人、未了心愿,醫生對患者的關注程度讓記者吃驚。
忍受巨大痛苦、耗費巨額資金,高繼峰覺得這不應該是疾病終末期患者走完生命最后一程的樣子。“在這里,患者每天的病床費和治療費不過幾百塊錢,且可以大比例報銷,不用昂貴的藥物和儀器也可以起到緩解疼痛的作用。此外每天都有家人、醫護人員和志愿者的陪伴,給予患者不脫離社會、不離開親人的心理慰藉。”
記者聽說,在這個安寧療護中心,有的患者見證了女兒的婚禮、有的患者第一次說出了愛、有的患者講述了人生的高光時刻,有的患者把最后一句感謝留給了醫生。
如何破解發展困境
人文、科學、經濟,安寧療護幾乎是疾病終末期患者最佳的治療狀態,然而開展這項服務的醫療機構寥寥無幾,面對人口老齡化的現狀,這項理念甚至沒有得到廣泛的傳播,原因何在?
采訪過程中,記者隨機采訪了一些路人問什么是安寧療護,得到的回答幾乎都是不知道,甚至有人問是不是就是安樂死。聊城市人民醫院主任醫師高杰從2011年便開始接觸安寧療護的理念,并在后續的十年里通過宣講、實踐推動這項事業發展,他告訴記者,不管是早期醫療機構的試水還是國家衛健委發文后推進的這幾年,都沒有讓這項工作遍地開花。
記者了解到,2004年,時任山東大學第二醫院麻醉科主任王志剛牽頭建立了臨終關懷病房,后來因為其工作調動病房隨之關閉。2009年,山東省千佛山醫院腫瘤科成立“寧養病房”,半年后也關閉。2016年,位于山東大學齊魯醫院東院區的舒適醫療綜合病房開始試運營,提供臨終關懷服務,但隨后停止了運營。
在國人的傳統觀念中,死亡一直是個避諱的話題。陳健鵬告訴記者,“我認為每一名臨終患者都有疾病的知情權,在經歷過逃避、憤怒、崩潰等情緒后會開始平和接納,那時的狀態更有利于患者安排自己的最后時光,對延長生命也會有幫助。”
另一個亟待轉變的理念便是竭力搶救。病人生命瀕危之時,常常會被送進重癥監護室,通過氣管插管、心外按壓、電擊除顫等措施進行搶救,這些措施都與痛苦相伴,會帶來創傷,且費用昂貴,動輒幾萬塊錢。即便如此,多數家屬在面臨“救”與“不救”的選擇時,還是會毫不猶豫地選擇“救”。曲亞敏說,當時拼盡全力救治母親,一方面是為了讓自己有個心理安慰,一方面是害怕家人的指責。“我不救,親戚可能會以為我不想花錢選擇了放棄,會覺得我不孝順。”陳健鵬覺得,曲亞敏代表了很多家屬的心態。
安寧療護病房關閉的另一個原因是繞不開的經濟賬。
采訪中,一些醫院工作人員坦言,安寧療護主張舒緩治療,治療費用較少,這樣的花費對于很多三甲醫院而言,毫無經濟效益可言,在床位緊缺的當下,這是不得不考慮的現實問題。另外,公立醫療機構提供的安寧療護服務,屬于治療、護理、檢查檢驗等醫療服務項目的,可以按既有項目收費,但屬于關懷慰藉、生活照料等非醫療服務的,至今沒有收費標準,但這部分卻是安寧療護中的重要內容。
陳健鵬認為,三甲醫院的定位在于治療各種疑難雜癥患者,作科學研究,同時向下級醫院分流病人,臨終患者在最后階段已無需高超的醫療技術,應該讓患者在適合的醫療機構接受最好的醫療服務。
顯然,高繼峰所在的二甲區級醫院是個不錯的選擇。高繼峰坦言,相較于大醫院的一床難求,很多二級醫院常年床位不滿,開設安寧療護中心后,越來越多的病人從大醫院分流或主動前來,對于經營上是個補貼。每一名來此的病人都能得到醫護人員細致的關照,生命的每一天都更有溫度。
記者了解到,醫院之間安寧信息不互通,患者家屬不知道哪里可以進行安寧療護。對此陳健鵬建議,應打破醫療機構間的壁壘,雙向評估病患與機構供需,建立高效專業的轉診機制,成立全省轉介樞紐平臺。
此外,相較于治愈患者的成就感,送病人離世的工作稍顯壓抑,很多醫護工作者不愿接受這項工作。山東大學法學院(威海)社會工作系馬艷朝博士表示,安寧療護是由醫生、護士、志愿者、社工及心理咨詢師等組成的專業服務團隊,對于社會工作者的需求量較大,但相較于上海、廣東等發達地區而言,山東相關的社會組織機構不足、發展空間不夠且不充分。面對需求,各方面人員都十分稀缺。
在幾天的采訪中,記者看到安寧療護中心的醫護人員幾乎一刻不得閑,其中開解患者、撫慰家屬情緒等工作占用了大量時間。
李大娘的主治醫師宋玉軍工作的前幾年,經歷了無數次的痛徹心扉與身心俱疲,她想過調離,直到一位臨終大爺留給她“您盡心了,我滿足了”這句話,她才真正明白了這份工作的意義。
“但醫生護士不能只靠著情懷支撐工作。”高繼峰直言,安寧療護中的非醫療服務沒有定價收費標準,但我們的醫生護士要耗費很多心力,他們辛勤的勞動很難得到物質體現。馬艷朝同樣認為,相較于其他省份,目前我省關于安寧療護的政策支持體系還未建立,包括醫保、配套資金等都亟待完善。
除了醫護人員,心理咨詢師、志愿者、社工等人員同樣需要不斷擴充。
在聊城市東昌府區中醫院采訪時,記者看到了20歲的大學生孫玉,他年紀雖小但從事志愿服務已有兩年。這兩年,越來越多像高杰一樣的醫生走進高校,將安寧療護的理念傳播給年輕一代,也有越來越多的年輕人關注、加入志愿服務。
在山東省立醫院,記者看到48歲的心理咨詢師李慧與一名患者進行了40分鐘的溝通交流,過程中她傾聽、提問、關切、建議,對話溫暖安寧。平日里她是一名幼兒教師,同樣是一名志愿服務老兵。
不管是20歲的孫玉還是48歲的李慧,他們給予患者的陪伴交流讓人感動,安寧療護急需更多志愿者的加入。
(為保護隱私,文內患者、家屬均為化名)
送一個人好好“走”,同樣體現醫生價值
□本報記者 常青
在動筆寫這個題目前,我思考了很久,擔心無人愿意交談與傾訴。事實恰恰相反,無論是從事這項工作的醫護人員、志愿者還是臨終期的患者及其家屬,都表現出了極大的善意與坦誠。他們都在向我表達一種想法:安寧療護應該被推廣,也希望被更多人接受。
無論是陳健鵬、高杰還是高繼峰、宋玉軍,他們都把安寧療護當作終生事業為之努力。正如采訪中提到的,這份工作幾乎無名無利,甚至得不到同行的認可,但患者和家屬的一句感謝,生死兩相安的溫暖結局,對于他們就是最大的回報。
宋玉軍告訴我,她從醫時最想做的是婦產科醫生,每天迎接新生命,是多大的成就感。如今從事安寧療護似乎是“背道而馳”,但幾年的工作下來,她覺得送一個人好好地“走”和迎接他來一樣重要,沒有高低,都是一名醫生的責任與價值。
通過很多安寧療護醫護人員的努力,很多臨終患者對于死亡不再恐懼,反而安排好一切安靜地面對人生最后階段,他們對醫護人員充滿了感謝,感受到了醫院從未有過的溫度,家屬改變了對醫生漠然生死的刻板印象,醫患關系朝著良性發展。
然而,正如高繼峰所言,從事安寧療護應該有情懷,有奉獻精神,若只憑著一腔熱情不足以讓這項事業開枝散葉,發展壯大。通過調查,我了解到山東早在1998年便開始開展安寧療護工作,但20多年過去,發展速度、規模、質量已落后于上海、廣東等地。做好此項工作,相應的政策制度配套支撐是第一位的,其次還需好經驗的借鑒傳播,需要更加廣泛的群眾接受度和參與度,需要全社會多個系統的支持配合。
令人欣喜的是,近兩年國家相關政策不斷出臺,為這一事業的發展提供了指引方向。及時跟進并制定適應實際情況的配套政策,是我省破解安寧療護發展困局的關鍵。

想爆料?請登錄《陽光連線》( https://minsheng.iqilu.com/)、撥打新聞熱線0531-66661234或96678,或登錄齊魯網官方微博(@齊魯網)提供新聞線索。齊魯網廣告熱線0531-81695052,誠邀合作伙伴。
濟南:清明假期12345熱線為民服務9.37萬件
- 記者從濟南市12345市民服務熱線了解到,4月3日-5日清明節假日期間,12345市民服務熱線共為民服務9.37萬件,較去年同期增長12.22%,日均為民服務...[詳細]
- 齊魯晚報 2021-04-06
拓展綠色能源空間 山東能源企業上演現代版"闖關東"
- 近日,由山東省能源骨干企業山東發展投資集團、水發集團、華能集團山東公司參與的“吉電入魯”200萬千瓦風電項目,獲得吉林省發展改革委核...[詳細]
- 大眾日報 2021-04-06
山東清明英烈祭掃紀念活動有情懷有溫度 580萬人現場祭英烈
- 山東清明英烈祭掃紀念活動有情懷有溫度。◆為1030位有名烈士和149位無名烈士找到親人◆首批提取744位無名烈士DNA樣本,成功比對出4位烈士信...[詳細]
- 大眾報業·大眾日報 2021-04-06
【回望歷史 緬懷先烈】山東:學黨史明初心祭先烈
- 本報訊(記者田國壘)“我志愿加入中國共產黨,擁護黨的綱領,遵守黨的章程……”近日,山東省淄博市周村區總工會在區職工黨性教育實踐基地...[詳細]
- 工人日報 2021-04-06

山東郵政與山東電信攜手助力“智慧山東”藍圖建設
- [詳細]
- 齊魯網 2021-04-05
這里春光無限好!清明小長假南山公園春游正當時
- 4月里,煙臺市城管局園林建設養護中心南山公園萬木爭春,鮮花盛開,為這座城市增加了不少春天的氣息。公園工作人員劉琥告訴記者,清明假期...[詳細]
- 膠東在線 2021-04-05
清明節小長假三天,市區處理生活垃圾8670噸!煙臺環衛給力!
- 假期三天,市區100%資源化處理生活垃圾8670噸(含蓬萊長島)。據了解,節日期間,為加強春季消防安全管理,市區兩級環衛部門提早謀劃,周密部...[詳細]
- 膠東在線 2021-04-05
清明假期煙臺接待游客33.32萬人次 實現營業收入1862.83萬元
- 膠東在線4月5日訊春和景明,惠風和暢。為讓廣大市民游客盡享煙臺春色和文旅盛宴,煙臺市文化和旅游局精心策劃、周密部署,著力豐富文化和旅...[詳細]
- 膠東在線 2021-04-05
清明假期搭乘地鐵出游成為濟南市民新選擇
- 3月26日,備受濟南市民關注的軌道交通2號線開通運營,換乘更加方便,與有著“開往春天最美的地鐵”美譽的地鐵1號線完美組合,清明假期搭乘...[詳細]
- 大眾網 2021-04-05
關注城市重大戰略!青島為出臺新版科技獎勵辦法公開征求意見
- 青島日報社/觀海新聞4月5日訊日前,市科技局發布新版《青島市科學技術獎勵辦法》征求意見稿。其中,市自然科學獎應當注重前瞻性、理論性,...[詳細]
- 青島日報社/觀海新聞 2021-04-05
濟南17家5A4A級景區清明假期共接待游客63.6萬人次
- 佳節清明桃李笑,萬條千縷綠相迎。今年“清明”小長假,市民游客出游熱情高漲。記者從濟南市文化和旅游局獲悉,濟南假日期間納入重點監測的...[詳細]
- 大眾網 2021-04-05
同比顯著增長!清明小長假青島十大重點商貿企業總銷售額預計突破4億元
- 青島日報社/觀海新聞4月5日訊今天下午,觀海新聞記者從青島市商務局獲悉,清明假期期間,全市各大商超、綜合體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前提下...[詳細]
- 青島日報社/觀海新聞 2021-04-05
煙臺市城管局排水服務中心組織開展清明節祭掃活動
- 膠東在線4月5日訊。在清明節到來之際,市城管局排水服務中心組織全體黨員到西炮臺愛國主義教育基地,開展“學黨史、祭英烈、守初心、擔使命...[詳細]
- 膠東在線 2021-04-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