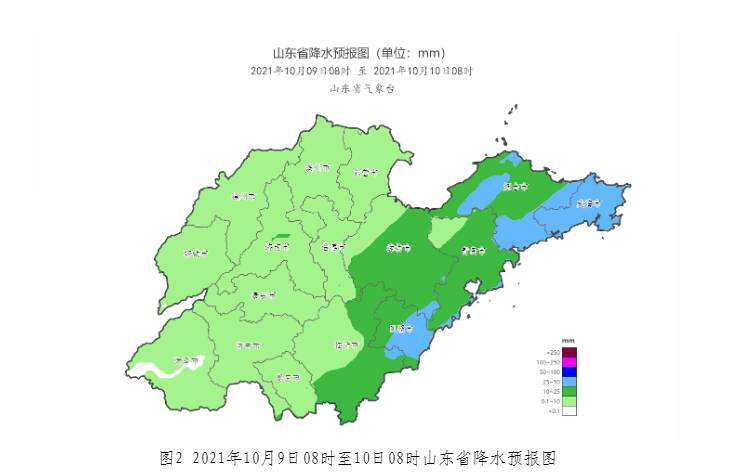魯迅誕辰140周年 解鎖其小說創作密碼
來源:北京青年報
2021-10-11 00:59:10
原標題:魯迅誕辰140周年 解鎖其小說創作密碼
來源:北京青年報
魯迅誕辰140周年 解鎖其小說創作密碼
周樹人何以成為魯迅
◎主題:周樹人為什么會成為魯迅?
◎時間:2021年9月25日19點
◎嘉賓:陳漱渝 魯迅研究專家,北京魯迅博物館前副館長
姜異新 學者,北京魯迅博物館研究室主任
“所仰仗的全在先前看過的百來篇外國作品”
姜異新:今天(魯迅生于1881年9月25日,編者注),魯迅先生140歲了。他在36歲的時候寫了中國第一部劃時代的現代小說《狂人日記》。在座的朋友們,可能率先進入你們視野的魯迅就是這樣一個小說家。
其實那時候他的本名叫周樹人,是北洋政府教育部的僉事。他有一個身份是通俗教育委員會小說股的主任和審核干事。當時全國所有創作的小說、翻譯的小說,乃至刊登小說的雜志,都要送到周樹人這里來評審——寫得好的小說要褒獎,格調低下的要查禁。工作之余,周樹人還抄校古籍,做《古小說鉤沉》,編《唐宋傳奇集》等,寫了第一部中國小說史,在北京大學等各個高校講授這門課。這么看來,在1918年《狂人日記》發表之前,也就是周樹人成為魯迅之前,這個人讀過的古今中外的小說實在是多到不可計數。
成為新文學之父后,也就是周樹人成為魯迅之后,經常收到文學青年的來信,討教作文的秘訣。魯迅的回答是創作沒有秘訣,并說自己從不看小說做法之類的書,只是多讀作品。1933年,應邀談一談創作經驗時,魯迅寫了《我怎么做起小說來》一文,終于道出了類似秘訣的經驗談——“所仰仗的全在先前看過的百來篇外國作品”。
然而,魯迅的小說閱讀太海量了,從留學回國到《狂人日記》發表之前,還有近十年所謂的沉默期,這期間其實他也在大量審讀小說。那么,我們如何去界定他說的“百來篇”?這就需要留意一下“先前”和“做學生時”——魯迅在各種語境下多次提到的時間狀語,其實指的就是1902-1909留學日本的這七年。我們知道,在江南水師學堂、江南陸師學堂附設礦路學堂讀書時期,是周樹人第一次接觸西學,課余時間也全部用來讀《紅樓夢》等中國古代白話小說。但在后來魯迅述懷的語境中,“先前”“做學生時”都特別指向留學日本這七年。“百來篇”指的就是這期間他用外語去讀的外國作品——一開始是通過日語的轉譯來閱讀,后來通過德語直接閱讀原版的東歐或者其他國家的小說。
那么,魯迅留日七年是如何度過的?他是怎么留學的呢?我們知道,魯迅在江南水師學堂接觸了英語,在陸師學堂的礦路學堂接觸了日語、德語,但還都很淺顯。獲得官費留學資格后,初抵東京的最初兩年,他是在弘文學院系統學習日語,學科知識相當于日本的中學程度。兩年后選擇專業,據他說為了救治像他父親一樣被誤治的病人,戰爭時期就去當軍醫。于是,他來到了位于日本東北部的仙臺醫學專門學校,學習醫學一年半。“幻燈片事件”后,再度回到東京,專心從事文藝運動,其實最主要的就是翻譯外國作品。他傾向于俄國、東歐、巴爾干小國被壓迫民族的作品,因為感到這才是為人生的、抗爭的、剛健的、赤誠的文學。這個時期最長,有三年之久。所以,魯迅留學時代影響了他精神走向的其實是海量的閱讀。這七年間,持續不間斷的學習行為就是閱讀和翻譯。
“從別國竊得火來,煮自己的肉”
姜異新:相比之下,仙臺時期少了點,但這個仿佛對文學閱讀按下暫停鍵的一年半,卻是不可或缺的橋梁。為什么這么說呢?清國留學生周樹人的外語水平在這個時候獲得了質的飛躍,無論是日語還是德語,也無論是口語還是書面語。我們都知道,藤野先生給魯迅批改醫學筆記,把他畫得特別好看的下臂血管給訂正了,但其實通覽醫學筆記,藤野的大部分修改是關于日語表達和修辭方面的。因為藤野先生那時候也剛剛評上教授,他還是副班主任,周樹人是他的第一個留學生,當然也是仙臺醫專第一個中國留學生,所以,藤野先生非常負責任。那時候也沒有多少教材和教輔書,所謂醫學筆記就是對老師課堂口述的筆錄。所以,老師講的課一定要非常認真聽,然后才能夠記下來,也沒有參考書去參照訂正。所以,藤野先生批得也特別認真。周樹人的日語口語、聽力和書寫便得到了極大提升。再就是他在仙臺醫專開始正規修德語課,課時也非常多,德語水平也有了很大提升。
今年是魯迅誕辰140周年,有很多大的文化工程結項,以向民族魂致敬。其中,國家圖書館出版社與文物出版社聯合編輯的《魯迅手稿全集》七編78卷也即將出版,這是歷來收入魯迅手稿最精最全的全集。在這78卷里,我認為最特別的就是醫學筆記,典型的用鋼筆從左至右橫寫的現代體式的筆記,里面有漢、日、德、英、拉丁等至少五種語言。而其他手稿可以說全部都是魯迅用金不換毛筆豎寫的傳統中國式手稿。當然,小字條不在比較之列。
從醫學筆記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索居仙臺在魯迅文學生命進程中的獨特性。隨著外語水平的提高,之前沒太讀懂的故事一下子心領神會了,一下子擺脫日語翻譯的中介限制,可以直接用德語去讀懂原版東歐故事了,對世界文學的渴求愈加強烈,想讀得更多、更深、更遠。再加上日俄戰爭的時事幻燈片在細菌學課堂上播放,因為日俄戰爭開戰的戰場是在中國的東北,只要是一個中國人,看到這樣的幻燈片沒有不受刺激的,當然也深深刺激了魯迅。
所以,內驅力加上外在的導火索,魯迅很快就輟學再度回到東京,要“從別國竊得火來,煮自己的肉”。我們知道,明治時期的日本是中西文化匯通、世界文學窗口的敞開地之一,信息傳遞非常迅捷,翻譯界更是立足世界前沿,引領社科思潮,很多世界著名文學家像向往巴黎一樣地向往到東京沉潛。魯迅也再次來到東京,開始了自主閱讀學習的三年。他已經不去專門的學校了,完全是海量閱讀的留學方式。而且他的二弟周作人也來到東京,周作人是非常精通英語的。所以我們尋繹的這“百來篇”包括魯迅用日語、德語讀的小說,也包括英語。實際上,魯迅在江南水師學堂就讀期間是接觸過英語的,他也能夠借助詞典、借助周作人的視野和幫助,去閱讀英文版的作品。
為什么留學日本時首先關注俄國文學
姜異新:再度回到東京的三年,魯迅下的功夫非常大、非常深,常常整夜不睡地閱讀翻譯外國作品,留在茶幾上的是像馬蜂窩一樣插滿了煙蒂的煙灰缸。魯迅所說的“百來篇”主要就是這一時期苦讀的作品。其實,初抵東京時期,周樹人就已經開始“盜火煮肉”了,開始翻譯外國科幻小說。只不過,他的肉身還沒有覺察心靈的渴求,還在順遂學校的選科制度,為未來的職業做出有限的選擇。而經過仙臺的轉換,一下子接通了文藝心靈的道交感應。
既然魯迅留學日本的七年以海量閱讀為主要學習方式,那么,他提到的“百來篇外國作品”到底有沒有一個詳細的書目?魯迅從來沒有明確地陳說。這就仿佛構成了一個謎,成為很多關注魯迅閱讀史、文學家魯迅創生史的學者們窮究破譯周樹人之所以成為魯迅的密碼。
我主要從五個方面依據入手來尋求、探索和推測。簡單說來:第一是剪報;第二是翻譯作品,特別是已出版的《域外小說集》,還有打算翻譯的出版預告;第三是周氏兄弟回憶文字;第四是文學教科書;第五是藏書視野下的經典周邊及潛在閱讀。通過探究,我發現至少有140篇外國作品是能夠與魯迅在留日時期通過外語讀過的外國作品掛上號的。
第一部分剪報,這是實實在在的物證,是魯迅從日本帶回來的日本人翻譯的十篇俄國小說的合訂本,包括屠格涅夫、普希金、果戈理、萊蒙托夫等作家的作品。但我不把它僅僅看成是一個剪報,我覺得這是魯迅以他自己的審美眼光編選輯錄的俄國作品集,也是他自己裝訂成冊為一本新書。我們對這十篇作品進行了故事的縮寫。
第二就是他翻譯的小說,這肯定是他反復咀嚼過的作品。這里我只提一下《域外小說集》里的16篇。我們看到,第一冊基本還是俄國文學占主體。為什么魯迅留學日本時首先關注俄國文學?我認為是日俄戰爭的巨大影響。這應該是魯迅最初關注俄羅斯文學的外部因素。在明治日本夢想著文明開化、富國強兵、領土擴張的國民昂揚感中,如何撥云見日、驅散迷霧,初步形成自己的俄羅斯觀,這是周樹人的獨立思考。其實俄國并不是后來他說的東歐弱小國家,而是西方的列強之一,周樹人要看看雄起于廣袤原野上的西方強國俄羅斯的土地上生長著怎樣的人民。一開始他只能通過日語去了解。其實他也學了幾天俄語,后來放棄了。當看到原來也有被侮辱被損害的小人物,也有被剝削到連短褲都沒有剩下的農民時,他反而獲得一種心靈得以深入溝通的藝術愉悅——這片土地上孕育的作家具有如此宏闊的視野,如此超然洞悉人性的筆力,產出了真正為人生的剛健的文學,促使他理解了在中國的土地上旋生旋滅的種種現象。
更多發揮工具書作用,體現領讀宗旨
姜異新:其實第二次來到的東京,對周樹人來說已經不是地方上的東京,而是世界的縮影,就像20世紀20年代的巴黎一樣,吸引眾多文藝家聚集在咖啡館形成一個文學群落,東京也具有吸引不少他國作家去沉潛的文化魅力。魯迅也是在這里集中閱讀了三年。連日本人的雜志都關注到周氏兄弟的閱讀行為,特別是他們要擺脫開日本,把外國故事直接用漢語介紹到中國去的翻譯活動。所以,《域外小說集》中的作品雖然魯迅只翻譯了其中的三篇,但是全部16篇都經過了他反復的審讀、潤色和修訂。這些故事我們組織學術力量,依據最初的東京神田版對周氏兄弟的文言譯本進行了白話重譯。
再一個就是文學教科書。再度回到東京這三年,雖然周樹人不去到全日制的學校上課,可是他也是把學籍掛在獨逸語學校。日本學者考證出了學校的文學教科書以及暑期閱讀的文學書目,我也對照館藏魯迅藏書書目,篩選出一些間接證明魯迅那時可能讀過的外國作品。
最后,就是通過周氏兄弟的回憶文字和其他線索推斷出來的作品,設為“其他”一輯。我們揀選了一些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進行了縮寫。比如,魯迅特別喜歡的夏目漱石、顯克維支,還有人們不那么熟知的克爾凱郭爾等等。
再次閱讀魯迅留學時代閱讀的故事,其實很容易發現他個性化的審美傾向——那些洞悉人性幽暗的作品,舉重若輕、讓人含淚微笑的表現手法,現代主義的意識流,后現代主義的英雄戲仿,對于被損害被侮辱的小人物的現實主義關懷,等等,顯然這是多維復雜的藝術綜合體,魯迅那個時候全部都接受了。編這本書之前,我會覺得魯迅真的是天才,而且不可復制,能夠用中國古代文人乃至近代以來的作家都意想不到的方式,在最簡短的篇幅內把故事講述得如此生動、深刻、直抵心靈;看了魯迅讀過的小說后,我就有一種豁然開朗的感覺,仿佛置身于魯迅當年置身的精神譜系的網絡當中,感同身受,與他一起感動,一起愉悅,審美能力一起成長,同頻共振。
遺憾的是,這本書僅僅收了有魯迅直接閱讀證據的38篇小說。其實,我們還縮寫了不少外國作品,限于篇幅,暫時沒有收入。當今是一個輕閱讀的時代,考慮到做一本非常厚的書,大家可能很難讀完。不過,在書的最后附了“百來篇”篇目的列表,除了作家作品的名字,還有魯迅閱讀的直接證據和間接證據。所以說,《他山之石》發揮的更多是工具書的作用,體現了領讀的宗旨——引領大家循著魯迅的目光去繼續探索、深讀原著原版小說。如果大家喜歡,以后可以再出續編,真正呈現給大家魯迅讀過的“百來篇”。
“欲新一國之民,不可不新一國之小說”
陳漱渝:今天,大家都承認魯迅是文學家,而為魯迅奠定文學家地位的則是他的小說。
而事實上,魯迅最初是通過翻譯活動走向文壇的,最早的成果是跟二弟周作人共同編譯了《域外小說集》。這本書得到朋友資助,在日本東京分上下兩冊出版,在上海市找了一個綢緞莊寄售。上冊印了1000本,賣了20本;下冊印了500本,也只賣了20本。后來這家綢緞莊著火,存書和紙版也隨之灰飛煙滅。這本書被冷落的原因之一,是因為當時的讀者還不習慣于短篇小說這種文體,不知為什么文章剛剛開頭就很快結了尾。中國人看慣了章回體,動不動要看八十回或一百二十回才過癮,看戲也要看連臺本。
中國讀者是通過魯迅1918年5月在《新青年》雜志發表的《狂人日記》才開始接觸現代短篇小說的。在中國古代,“小說”這個名詞概念不清,又缺乏科學分類,但實際上存在著文言小說跟白話小說這兩個傳統。直到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從油印講義到學術專著,中國古代小說的發展才被梳理出一個粗略的歷史輪廓。所以魯迅1923年10月7日在《中國小說史略》中寫道:“中國之小說自來無史……此稿雖專史,亦粗略也。”
1918年4月19日,周作人在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小說研究會發表演講,題為《日本近三十年小說之發達》。周作人說,在中國傳統觀念中,寫小說是一種下等行為。1902年,梁啟超發表了《小說與群治之關系》一文,提倡“小說界革命”,把小說視為改良社會政治的重要工具。文章開頭第一句話,就是“欲新一國之民,不可不新一國之小說”。由于新小說可以培養國民新型的道德和人格,激發國民的愛國精神,達到改良政治的目的,所以“為文學之最上乘”。上乘就是上等。
但是,雖然有梁啟超大力倡導,“新文學的小說卻一本也沒有”“算起來卻毫無成績”。因此,周作人希望中國的小說家能借鑒日本小說的創作經驗,這經驗用五個字來概括,就叫作“創造的模擬”。周作人所說的“模擬”就是我們所說的“借鑒”。“創造的模擬”就是在借鑒的基礎上加以創新、實現跨越。中國的新小說不僅要具有新的形式,同時也必須表達新的思想,這就需要從頭做起。我認為周作人這種新小說觀,魯迅也是認同的。如果說,胡適和周作人是中國現代小說的理論倡導者,那么魯迅就是這種理論在創作領域的開拓者和奠基人。
魯迅創作的小說并不多,結集出版的只有《吶喊》《彷徨》和《故事新編》這三種,一共收錄的作品33篇。我以為,僅憑《阿Q正傳》這一篇就可以使魯迅在“文學家”這個稱謂之前再加上“偉大的”這個定語。阿Q這個精神典型很快大踏步地進入了世界文學典型人物的畫廊,所以魯迅也就成為了世界級的作家。他不僅屬于中國,而且屬于人類。
《他山之石》為魯迅研究提供新的學術增長點
陳漱渝:創作小說,首先要有堅實的生活基礎,豐富的人生閱歷,深邃的思想穿透力。但同時還必須汲取中外文化滋養,否則就成了無源之水,無本之木。魯迅在《我怎么做起小說來》這篇文章中明確說過,他創作小說之前并沒有讀過“小說作法”之類的理論書籍,而“所仰仗的全憑先前看過的百來篇外國作品和一點醫學上的知識”。眾所周知,魯迅在日本仙臺醫學專門學校學過醫。他塑造《狂人日記》中那個“迫害狂”的形象,就仰仗了一些神經內科方面的知識。
至于他以前究竟讀過哪“百來篇”外國小說,我原先覺得是一個永遠解不開的謎。離開了人證、物證、旁證,誰有本領開列出這百來篇外國小說的篇目呢?從1989年起,我開始研究魯迅藏書,并發表了一些短文。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我又申報了一個集體科研項目,就叫《魯迅藏書研究》。我的同事、師姐姚錫佩在查找魯迅收藏的剪報時,發現了一冊裝訂好的日譯外國短篇小說,這就是魯迅留日期間閱讀日譯外國短篇小說的物證。這一發現增強了我探尋魯迅1918年之前所接觸的百來篇外國小說的濃厚興趣。從那時到現在,差不多是30年了。所以,我說《他山之石》的出版,是實現了我30年來的一個夙愿。
如果從1909年日本東京出版的《日本及日本人》雜志第508期,報道周氏兄弟的翻譯活動算起,魯迅研究已經有了112年歷史。經過一代又一代魯迅研究學者的共同努力,魯迅研究已經成為了一門相對成熟的綜合性學科,也可簡稱為“魯迅學”。這門學科的史料已經基本齊備,今后很難再有能產生轟動效應的發現。對魯迅評價也基本正確,很難產生顛覆性的看法并能在魯研界占據主流。
對魯迅作品闡釋當然空間無限廣闊,但魯迅對自己的很多代表作已有自評,研究者對這些作品的理解也很難超越魯迅本人的自我認知。所以,魯迅研究學科水平的提升可以說是遇到了一個瓶頸,致使有的學者知難而退。有個別學者則通過過度闡釋或故意曲解的方式嘩眾取寵,吸引大眾眼球。
《他山之石》的出版,為魯迅研究提供了一個新的學術增長點。讀者不應該僅僅關注魯迅哪篇小說受到了哪位作家的具體影響,比如《狂人日記》的篇名取自果戈理的同名小說,《藥》的結尾有安特萊夫似的陰冷……這樣的例證是有限的。我們應該通過閱讀這本書,進一步研究魯迅在創作中國現代小說時在文體上進行的大膽探索,比如《狂人日記》《阿Q正傳》《一件小事》《頭發的故事》為什么形式都很不一樣?特別是《故事新編》,為什么又采取了古今穿越的手法?魯迅對這些外國小說精神上的繼承和發揚更值得關注。魯迅講得很明白,他在外國文學作品中尋求的是反抗和叫喊的聲音。他從俄國文學作品中明白的大事是世界上有兩種人——壓迫者和被壓迫者。所以,我們從魯迅的閱讀和翻譯的文化取向中應該學習的首先是魯迅的平民立場,以及對惡勢力的斗爭精神。這在任何時代都是為人處世的基本素質。整理/雨驛

想爆料?請登錄《陽光連線》( https://minsheng.iqilu.com/)、撥打新聞熱線0531-66661234或96678,或登錄齊魯網官方微博(@齊魯網)提供新聞線索。齊魯網廣告熱線0531-81695052,誠邀合作伙伴。
“看空”中國經濟者何以頻頻“落空”
- “看空”中國經濟者何以頻頻“落空”。然而,中國經濟持續向好,發展成就舉世矚目,“看空”中國者被中國經濟的實際表現一再“打臉”。推動...[詳細]
- 北京青年報 2021-10-11
萬類霜天競自由——寫在《生物多樣性公約》締約方大會第十五次會議開幕之際
- 萬類霜天競自由——寫在《生物多樣性公約》締約方大會第十五次會議開幕之際新華社昆明10月10日電題 萬類霜天競自由——寫在《生物多樣性公...[詳細]
- 新華網 2021-10-11
《生物多樣性公約》締約方大會第十五次會議即將開幕
- 《生物多樣性公約》締約方大會第十五次會議即將開幕。新華社昆明10月10日電《生物多樣性公約》締約方大會第十五次會議(COP15)第一階段會議...[詳細]
- 新華網 2021-10-11
食品名城,字圣故里——漯河
- [詳細]
- 漯河市文化廣電和旅游局網站 2021-10-10
打卡網紅辣條衛龍生產基地 探尋互聯網時代品牌如何“出圈”
- [詳細]
- 大象新聞 2021-10-10
雙匯食品的發展秘籍:智能化生產線助力產業升級
- [詳細]
- 河南電視臺《都市報道》官方微博 2021-10-10
漯河食品職業學院:打造食品產業公共研發平臺
- [詳細]
- 大象新聞 2021-10-10
新華時評:小家政撬動大戰略
- 新華時評 小家政撬動大戰略。未來五年,家政服務業迎來發展新機遇。商務部等14部門9日聯合印發《家政興農行動計劃》,提出7項22條工作舉措...[詳細]
- 新華網 2021-10-10
全國40余家主流媒體齊聚河南!感知中原脈絡 共繪小康新圖
- [詳細]
- 齊魯網 2021-10-10
漯河城市展示館:走進一座館 讀懂一座城
- [詳細]
- 大象新聞 2021-10-10
我們的共同家園|COP15大會主題宣傳片
- [詳細]
- 央視網 2021-10-10
把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偉業推向前進——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辛亥革命110周年大會上的重要講話引發強烈反響
- [詳細]
- 央視網 2021-10-10
小浪底等3大水庫水位創歷史新高 秋汛防洪處最關鍵階段
- 10月10日拍攝的黃河小浪底水庫泄洪場景。新華社北京10月10日電(記者劉詩平)水利部10日發布汛情通報,今年黃河、漢江和海河流域發生多年不...[詳細]
- 新華網 2021-1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