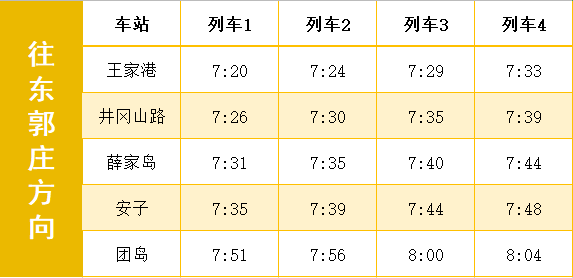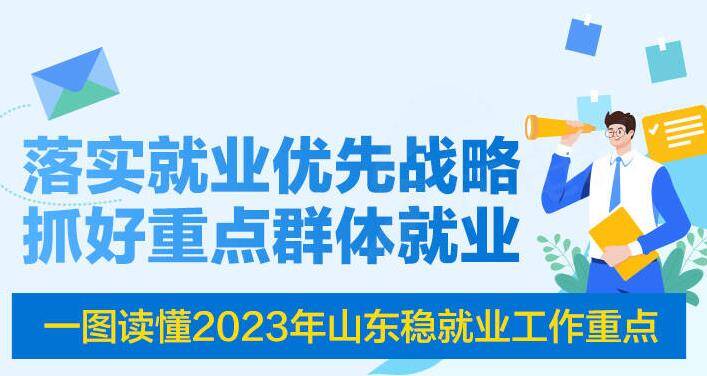晚清數千鐵匠,緣何移聚煙臺?
來源:煙臺晚報
2023-03-20 08:52:03
原標題:晚清數千鐵匠,緣何移聚煙臺?
來源:煙臺晚報
原標題:晚清數千鐵匠,緣何移聚煙臺?
來源:煙臺晚報
宋世民
一百多年前,煙臺打鐵業從釘掛牲畜的蹄鐵興起。在煙臺港開放后,鐵匠們的業務范圍逐漸擴大,由鍛打蹄鐵擴大到鍛造農具、豆餅模子等物件。打鐵業需求大增,導致外來鐵匠數量急劇增加,從業人員從1882年的約500人增加到1891年的約5000人,十年間擴大了十倍。據東海關統計,1891年煙臺城市人口總數約32500人,那么打鐵業人口約占總人口的六分之一。
這么短的時間,為何會有數千鐵匠移聚煙臺?
煙臺港開放后,打鐵業成熱門行當
查閱史料發現,依芝罘灣地理特征自然構成的煙臺港,雖然周圍沿岸灘平水淺,但其縱深陸地卻是丘陵地帶,進出通道坎坷曲折,有些地段“山路險僻至不能通騎”。囿于通往腹地陸路交通不便,港口物資在陸路集疏便只能靠牲畜和人力運輸了。
清同治五年(1866年),登萊青道道臺、東海關監督潘霨為改善港口腹地的交通條件,下令整修煙臺至黃縣的道路,即所謂煙黃大道,修好后使較多的輕便商品可通過此路運往內地。然而,這條大道畢竟是在山間小路的基礎上改建而成的,投入使用后又長期沒有得到維護,煙臺港的貨物疏運并沒能從根本上得到太大改善。
當年的目擊者曾留下不少記錄,從不同角度,陳述了那個年代煙臺陸路運輸的艱難狀況——
“轉運的交通工具僅是騾子、驢和馬以及笨重的車。他們吃力而且很慢地沿著所謂的公路行走,時常出入于被雨水沖垮的道路上。這些路面已被雨水沖得沒有東西了,只剩下巖石塊和凹凸不平的表面,甚至對腳步穩的騾馬來說都是很難通過的。在缺乏道路和河流的情況下,主要依靠這種慢而花費多的轉運。”
當時幾乎所有進出煙臺的貨物都是由馱畜運載的,每天有成千匹騾馬進出煙臺。開埠數十年后,這種運輸方式仍未改變。能夠行駛大車的,只有通往濟南府的一條大路。大車的用量很少,僅限于煙臺附近,要想通過城鎮外面的陡峭山嶺以及在城鎮里的街道通行,都是非常困難的。
史料記述:“在夏季和冬季,當其它運輸工具不能使用時,在丘陵地帶,馱畜就引人注目了。馱畜每天普遍走100里地,各自馱200~300斤的貨物。這一運輸方式的主要問題是裝貨時必須小心,兩邊重量必須相等,途中休息時必須卸下來,不然很可能被打翻……”
據東海關統計,每天有數以千計參與路運的人進出煙臺,而往返于路途之中的人數大大超過這個數字。每天進出煙臺的牲畜數量,約有三千匹。
從煙臺港開放之初至19世紀末,還有一種通過水路運輸疏散進口貨物的方式。清同治年間,“進口到本地的大部分商品由平底中國帆船運往大清河,在離該河口不遠的地方換載,即換到吃水淺的當地船上,運往內地的許多市場,其中最重要的有濟南府、東昌府、兗州府、曹州府、東平府,甚至運往直隸的大名府”。煙黃大道修整完畢之后,一些輕便的商品通過陸路運往內地,而價值較小且笨重的貨物則由船只上溯大清河。自清光緒十三年(1887年)小清河疏浚之后,“內海商輪、民船運載客貨,每由煙臺出海經過蓬萊縣之天橋口,黃縣之龍口,掖縣之虎頭崖,抵羊角溝,換乘小船,取道該河上駛,經過坌河石村,直抵濟南省城東關之黃臺橋”。
由于水路運輸價格稍低,而且運輸速度較快,因此不少貨物常常不走陸路而走水路,經大清河、小清河、濰河等幾條入海河流進入內陸。當時,大約有2500艘帆船往來于煙臺港與山東沿海各小港之間為煙臺港集疏貨物。
為這樣一支水陸并驅、人員眾多,所用器具種類繁雜、數量巨大的運輸隊伍,長年進行損耗補充、維修保養,絕非單一行業少數工匠能夠承擔。在各類消耗材料中,鐵件數量所需最多,需要鍛鑄的蹄鐵、車架鐵件、船釘、扒鋦、鐵錨等,都離不開大量工匠持續生產和裝配。
開埠前,煙臺域內已有鐵工、木工和筐簍編制業,為往來船只生產釘子、扒鋦、鐵錨和魚筐等,后逐步發展到生產小農具及木工工具。當時煙臺人口稀少,1860年尚被稱為“海隅僻處”,處于自然經濟狀態,這種使用簡單工具操作的家庭手工業,依舊從屬于農業。
當時,煙臺這處自然港灣,不僅是海上運輸線站點,更是河海聯運與水陸聯運的樞紐,以原來極其薄弱的生產能力,難以應對開埠后大規模運輸業的后勤需求。于是,山東域內的鄉村鐵匠,為獲取這份一年四季有活干、能養家糊口的職業,肩挑車載簡陋的生產工具,絡繹不絕奔赴港口附近擇地落腳,使煙臺從事打鐵業群體短期內迅速擴大,成為少數能夠吸納大量勞力的熱門工種。
各地鐵匠移聚煙臺“抱團”謀生路
數以千計的牲畜長年奔走在坎坷山路,蹄上鐵掌磨損很快,承擔打掛蹄鐵的工匠須臾不得缺失。這項平時并不被特別關注的工作,將大批原在農村半工半農的各類鐵匠,吸引到市鎮專事鍛制蹄鐵生意。一時間,煙臺街頭巷尾隨處可見鐵匠棚及為牲畜更換蹄鐵用的原木門架。
早期的蹄鐵多由為牲口釘掛蹄鐵的工匠自己打造。蹄鐵看似不起眼,形狀也不盡相同,成品分大、中、小三個規格。馬和騾的蹄鐵一邊都是三個釘孔。驢掌少一些,兩個釘孔。牛是兩半掌,所以蹄鐵不能U形,而是要釘掛兩塊鐵。蹄鐵的厚度約1厘米,釘子是楔形專用釘,釘尖是扁的,長約3厘米。
這些在釘掛蹄鐵時還需隨時修整的小鍛件以往消耗不多,由釘掛蹄鐵工匠自制比較方便,后來用量劇增,自家難以承擔,便逐漸改由烘爐鐵匠專業批量生產。
別看單只蹄鐵用料不多,要滿足數千匹馱畜的損耗,原材料需求數量也不小。廢舊鐵是打鐵業的主要原料,山東原有鐵業主要依靠山西供鐵。自1873年后,鐵匠們在實踐中發現洋鐵質量較高而且韌性也比較好,寧肯購買70銅錢一斤的洋鐵,也不愿節省20銅錢去買省內及山西生產的土鐵。到19世紀70年代末,煙臺港廢舊鐵每年進口已近3萬擔。在1879年東海關檔案中留下這樣的記錄:“據說為了獲得這種廢舊鐵,英國的舊鐵店都被搜掘一空,并且預定了來年的貨。這些舊鐵均按需要加工,其中許多是用來制造本地馱畜的蹄鐵。”
這一時期,煙臺的鐵匠和蹄鐵匠主要來自萊州。1862年,登萊青道由萊州移駐煙臺,原本在衙門駐地謀生的蹄鐵匠們,借海口開放之勢,不失時機隨貨運馱幫同步遷移,使打鐵業中心逐漸由萊州轉向了煙臺,成為相繼移聚煙臺的鐵匠群體先驅。后來,隨著造船業及營運船隊的發展,制作木船的工具,如斧頭、刨錛、鑿鏟以及日常生活中的鐵制用具大量增加,煙臺附近各縣擅長不同技藝的打鐵匠人,也陸續來煙臺攬活謀生。
當時域內從事其他行業的人口也不斷增加,使打鐵工匠占市區人口比例逐步縮小,但是,這一群體隨著海港運輸及城鎮發展的需求,從業人口總數仍然與日俱增,屬煙臺域內人口增長的主要成分。
這些來自不同地區的鐵匠,以縣域或相鄰地區為單位自發組合,逐步散居在市區許多街巷。被稱為“萊州幫”的烘爐鐵匠,大多在毗鄰太平灣的大關前街附近落戶。以威海、榮成人為主的烘爐鐵匠,多聚集在西南河口兩岸開店立戶,專事船具、鐵錨生產,時人稱其為“威榮幫”。專門打制刃具、菜刀、魚刀、鍘刀、紙刀的“章丘幫”鐵匠,多居住在南洪街、四道灣一帶。專門打鎖鏈、鐵锨、火鏟、勺子、剁銼等小鐵件的“濰縣幫”,多居住在毓璜頂下的百業市場附近。專門生產家用剪子、鐵剪子、理發剪子等各種剪刀的“臨沂幫”,則密居于大海陽宴芳街周圍,故其街得名“打剪子胡同”,與同期形成的“勺子胡同”“鐵爐巷”等街名一起,見證了當年打鐵行業的興旺景象。
有史料記述,在夜間,當這些勤勞的手工業者干活時,爐火將烘爐附近的夜色照得通紅。真個是“爐火照天地”,一簇一團,隨處可聞錘子擊打在鐵砧上的叮當響聲。正是這些背井離鄉的外地鐵匠,日夜艱辛勞作,以傳承千百年的鍛造方式,構成當時城鎮初級物流系統的重要環節,為港口貨物集疏運輸提供了后勤支持,也為后期煙臺手工業乃至輕工業發展奠定了基礎。
最苦是鐵匠,出路在哪里?
烘爐均無廠房,多是露天作業,在煙臺開埠后的幾十年里一度星羅棋布,僅西南河口附近、毓璜頂、東馬路、二道街一帶就有130余家。
鐵匠們多是四五人組合,師傅掌鉗,徒弟打錘。這種看似沉重又簡單的行當也有其傳統規則,雖因區域有別,但大體相似。如鐵錘擊打就分頭錘、二錘、三錘,有時三錘由雜工兼顧。掌鉗師傅的小錘呈扁形,鐵合金制作,敲起來特別響,俗稱響錘。這響錘就是指揮棒,點哪兒大錘就砸向哪兒,要打得準、力度大、有節奏,“當咚咚、當咚咚”持續不斷。若響錘不敲鐵塊,而是快速敲鐵砧,這是快打信號,掄大錘的徒弟就要加快擊打速度。當響錘敲在鐵砧耳子上發出“嘟嚕嚕”的聲音時,這是停止敲打的信號,大錘即停。
這些一年四季披星戴月辛勤操勞的鐵匠們,生產環境及生活條件是極差的。徒工們白天汗流浹背地掄大錘,一錘下去火星四濺,落到衣服上就是個洞,落到身上結個疤。夜晚就睡在滿是鐵屑、煤渣的烘爐旁。
有女不嫁打鐵郎,成年累月守空房;
正月初三去出工,出門帶的狗干糧;
臨走難湊盤腳錢,跪了二叔求大娘。
外出一年無音信,愁的青絲掛寒霜;
離家兩載不捎錢,家中老小炊斷糧;
出走三年無蹤影,多半尸骨埋他鄉。
夢里相約見一面,醒來淚水灑土炕;
又恨又氣鐵匠漢,活該你去見閻王。
當時鄉間流傳的這首歌謠,是這個群體生活和社會地位的真實寫照。
進城從業的徒工處境就更艱難了,辛苦一年,有的過年竟吃不上一頓餃子。煙臺德豐爐的窮兄弟曾留下這樣一首歌謠:
鐵錘叮當響,晝夜辛苦忙;
煙熏又火燎,爐前汗如漿。
累斷脊梁骨,難養爹和娘;
三百六十行,最苦是鐵匠。
在白、黑、紅三類鐵匠中,更苦的是那些以打制水桶、水壺、煙筒、撮子、籠屜、水舀子為主的鐵匠鋪徒工。這些小學徒多是家庭生活拮據,為家里少個吃飯的出門學徒,平日挨打挨罵也得忍受。
1946年5月25日,煙臺第一次解放后創刊的《煙臺日報》,曾在頭版刊發過一條題為《大關街鐵匠學徒改善了待遇》的消息,文中有徒工孫小喜對敵偽時期生活狀況的一段哭訴:“咱房無間,地無垅,父親拉的饑荒無法還,讓財主撞進井里灌死了。我11歲到鐵匠鋪學徒,每天雞叫起來干活,直到天黑,晚上還得干零活。凈吃些花生餅、豆餅及橡子面……”
新中國成立后,這個身處社會底層、飽受困苦的鐵匠群體,終于獲得了勞動者應有的社會地位。經過合作聯組、公私合營的社會主義改造,單干戶逐步歸集到大集體,到1960年前后,域內烘爐鐵匠集中到煙臺木瓦農具社、煙臺刃具社和煙臺剪刀社這三個手工業管理局的大集體企業中。
從那時起,那些自古以來便以手工體力勞動為主的烘爐鐵匠們,陸陸續續放下手中沉重的大錘,生產方式一步步走上機械化操作,成為煙臺輕工業發展的重要基礎力量之一。
想爆料?請登錄《陽光連線》( https://minsheng.iqilu.com/)、撥打新聞熱線0531-66661234或96678,或登錄齊魯網官方微博(@齊魯網)提供新聞線索。齊魯網廣告熱線0531-81695052,誠邀合作伙伴。
開花石成了煙臺網紅景點
- 昨日上午,記者打卡開花石一探究竟。“煙臺版愛樂之城”“泰山煙臺分泰”成了開花石在幾大短視頻平臺“爆火”的熱門詞,引來無數人前來打卡...[詳細]
- 煙臺晚報 2023-03-20
威海簽約國家水上休閑運動推廣項目
- 近日,國家水上國民休閑運動推廣暨槳板項目推廣簽約儀式在威海舉行。環翠區人民政府、哈爾濱工業大學(威海)、威海瑞陽船艇有限公司分別與國...[詳細]
- 齊魯晚報 2023-03-20
山東省反興奮劑工作會議召開
- 3月17日,2023年山東省反興奮劑工作會議在省體育訓練中心召開。會議總結近年來我省反興奮劑工作情況,對下階段工作進行部署。會議強調,我省全...[詳細]
- 齊魯晚報 2023-03-20
第五屆山東省老運會健身氣功賽舉行
- 3月16日上午,第五屆山東省老年人運動會健身氣功比賽在棗莊市新城文體中心體育館開幕。本次比賽共有來自全省各市、省直機關18支代表隊的210...[詳細]
- 齊魯晚報 2023-03-20
世錦賽獲1金1銀山東短道速滑再突破
- 在近日完賽的世界短道速滑錦標賽上,我省運動員李文龍搭檔隊友勇奪男子5000米接力金牌。加之此前我省李文龍、公俐在男女2000米混合團結接力...[詳細]
- 齊魯晚報 2023-03-20
寧津德百雜技蟋蟀谷榮獲山東省“管理和服務創新先進單位”榮譽稱號
- 近日,山東省旅游行業協會公布“管理和服務創新先進單位”獲獎名單,寧津德百雜技蟋蟀谷榜上有名。建有雜技蟋蟀谷、古建木雕園、玉博物館、...[詳細]
- 大眾網 2023-03-19

創新+轉型發展 山東港口物流集團再拓版圖
- 近日,山東港口陸海國際物流集團(以下簡稱“山東港口物流集團”)首票城市配送業務順利達成,標志著山東港口物流集團正式打響城市配送業務...[詳細]
- 海報新聞 2023-03-19
瞄準“產業+”,山東搶灘人工智能
- 瞄準“產業+”,山東搶灘人工智能人工智能。應用規模持續擴大,平臺引領推動發展成效明顯。記者從省工業和信息化廳了解到,山東同時擁有濟...[詳細]
- 中國山東網 2023-03-19
達成初步意向1717人!“山東—名校人才直通車”黃河行活動成功舉辦
- 中國山東網-感知山東3月19日訊。本次活動由省委組織部、省人力資源社會保障廳、西安交通大學、蘭州大學、東營市委市政府聯合舉辦,精心組織...[詳細]
- 中國山東網 2023-03-19
太平人壽淄博中心支公司榮獲“2022年度消保工作先進單位”榮譽稱號
- 淄博新聞網訊(記者崔曉蕾通訊員任涵)近日,淄博市保險行業協會對2022年度消保工作先進單位、優秀個人及糾紛調處突出單位和個人進行表彰。...[詳細]
- 淄博新聞網 2023-03-19
平安人壽淄博中支:上門服務保障老年金融消費者權益
- 淄博新聞網訊(記者崔曉蕾)近日,平安人壽淄博中支為不便到柜臺辦理業務的王先生上門服務,為其解決了問題,受到了客戶的好評。據了解,王...[詳細]
- 淄博新聞網 2023-03-19
45萬人報考!山東省2023年度事業單位初級綜合類崗位公開招聘筆試順利舉行
- 本次筆試共45萬人報考,全省共設371個考點、1.5萬個考場。在教育、工信、公安等部門的大力支持下,各級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門統籌協調、周密...[詳細]
- 中國山東網 2023-03-19
“巔峰時刻”山東省電子競技大賽在煙成功舉辦
- 膠東在線3月19日訊。3月18日下午,由山東省體育局、山東省體育總會主辦,山東省電子競技協會、煙臺市體育總會、煙臺市教育局黃渤海新區分局...[詳細]
- 膠東在線 2023-03-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