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三十年 成都現存最早的土地契約
來源:新華網
2018-12-30 04:29:12
在成都市房產信息檔案館、龍泉驛區和新都區等檔案局(館)留存下來的土地契約中,目前發現最早的土地契約,留存在成都市房產信息檔案館中。
康 熙 30 年(1691)二月十八日,哈榮盛“今因乏銀使用,闔家相商,愿將祖遺成邑東御街中段空地一塊,憑證出賣與清真東寺管業”。
土地契約中寫道:“(產業)實取賣價銀五十兩正,賣主一手收清,并無分厘下欠。自賣之后,任憑買主挖高補低,修造房屋,賣主不得異言。”
對這塊空地的界址,契約中也寫得很清楚:“其界東與馬姓為界,南與河心為界,西與郭姓為界,北與街心為界。四界分明,毫無錯亂。”
為防止交易后再生是非,契約中還約定:“其地自賣之后,哈姓家族人等不得異言。若有他故,惟賣主是問。其地一賣千秋,永無贖取。恐口無憑,特立賣約一紙,交清真東寺收執,永遠為據。”
壹
《祖遺》空地 天府廣場旁黃金地段
在契約上簽字畫押的有保正1人、街約1人、甲長1人、鄰居4人、中證2人、代筆1人。
這份契約,有買賣雙方、產業四界、交易金額、交易時間和見證人等,行文簡單,對產業的描述較為簡略,看不出來這塊空地到底有多大面積。
這與后來的契約趨于明細、對所買賣房地產的結構、材質、鋪院形態、四界位置、庭園果木等詳細注明,是有明顯區別的。
眾所周知,明末清初時,四川遭受了一場大浩劫,長期處于大規模戰爭中:先是張獻忠起事入川,后來又入蜀建立大西政權;張獻忠死后,殘部孫可望、劉文秀與明軍戰火不斷,后又在川北與清軍激戰;清軍最后得勢,清剿農民軍,搜捕明軍殘余;吳三桂叛亂,攻入四川,清軍平叛……
這些戰爭前后持續數十年,四川人口銳減。直到 康 熙 20 年(1681)底,四川境內的戰爭才算結束。據康熙24年(1685)的人口統計,經過大規模戰事的四川,川西人口只有9萬多人了。
康熙 33 年(1694),康熙帝正式頒布“招民填川”詔書,持續上百年、轟轟烈烈的湖廣填四川大型移民運動拉開序幕。
這份土地契約,是在四川境內戰爭停息10年后、“湖廣填四川”前3年簽訂的。而且,賣主哈榮盛在契約中明確說這塊空地是“祖遺”下來的,位置在今成都城區天府廣場側邊,典型的黃金地段。這表明,隨著當時成都社會經濟的逐漸恢復,成都城區內的居民已經開始了新的生活。
這份看似簡單的土地契約,對研究當時成都的社會經濟情況,具有一定的史料價值。
貳
典型契約 4500兩銀子買下120畝地
在成都市龍泉驛區檔案局(館)留存的賣地定金契約中,有一份契約可謂是目前所有土地契約中最大宗的一筆交易,交易總金額高達紋銀4500兩。
同治3年(1864)八月十三日,謝竹屏、謝銳臣“情因移窄就寬,弟兄商妥,將己名下”總面積為120畝多的兩段水田、一所基址、一塊旱地,連同所有住宅、瓦房“五向共十七間……一并隨田搭賣,毫無提留”,出售給蘇國寬。
簽訂賣地定金協議的同時,蘇國寬交定銀100兩,“在正價內算。賣主不賣,得一賠十;買主不買,定銀全丟。”
如此大的一宗土地交易,非同尋常,僅僅中間人就多達12個。
仔細分析這份定金契約會發現,這宗交易并非是單純的土地交易,而是混搭了房產等在內。土地是主要的交易對象,房產是附加在土地上的,沒有單獨核算價錢,即所謂“捆賣”。
交易總金額高達4500兩紋銀,這可不是一筆小數目。那么,這筆交易為何能達成呢?
在農村,能擁有120畝土地的人,除大家族外,僅僅是兩兄弟的家庭,其經濟實力再差也差不到哪去。更何況,他們的房產是17間瓦房。
在那個年代,農村住房一般都是草房,瓦房是比較少見的,就好比現在的別墅。
從賣地原因來看,謝氏兄弟不是缺錢用,而是因為有了更好的發展前途。“移窄就寬”表明,他們有可能搬家到城鎮去生活了,所以把農村的產業全部賣掉。
再來看買主。龍泉驛區檔案局(館)檔案編研負責人胡開全說,蘇國寬是居住在成都東山如今十陵街道青龍村青龍埂的大望族蘇氏家族的代表人物。
蘇氏家族財力雄厚,蘇國寬的父親蘇邦賢曾在30年里,在龍泉驛一帶買了上千畝水田,花去兩萬多兩銀子。
如此一個富豪型家族,靠著良好的經營方式,在蘇國寬時代,仍在繼續往上升。那個時代農村大望族積累財富的方式,買地是重要的手段之一。
所以,看起來是一筆巨款的4500兩銀子,蘇國寬是有魄力拿得出來的,而且是現貨交易,定金直接就是100兩。
一個真心實意想賣,即使把價值不菲的房產捆綁在土地中也不覺得吃虧;一個是鐵了心要買這宗優質產業,即使是出價4500兩也毫不猶豫。這樣一來,你情我愿,這筆交易就成了。
這筆交易從另一個角度反映出當時的社會現實:農村的富豪財主,通過貨幣購買方式,大量進行土地兼并,造成土地流轉向少數人手里集中。
或者說,財富向少數人集中,這樣下去的后果是,社會的貧富差距越來越大。
叁
同一宗土地21年增值1210兩
道光23年(1843)正月二十四日,寡婦雷楊氏與3個兒子雷一文、雷一興、雷一成,以及侄孫雷聲文、雷聲煃、雷聲肅,“情因各負外債,無銀償還,是以母子、弟兄、叔侄商議,甘愿將祖遺留溫江縣二甲,地名板板橋側近”的一份田業出售。
這份產業有97畝多田,“河邊溝坎基地約計二十畝零”,以及坐房二院,“瓦上房二向”共10間,“瓦廂房二向”共12間,糞房、牛欄、豬圈共14間,接簷3間,水井兩口,糞池8個,河邊草房兩處共6間,以及其附著物,全部賣給謝六樨堂,總價為九七三色紋銀3290兩。
21年后,謝六樨堂的謝竹屏、謝銳臣兩兄弟,把這份產業賣給蘇國寬,賣了九九色紋銀4500兩。
謝六樨堂從雷家買下這份產業后,到賣給蘇國寬,產業還是發生了一定的變化。
在田產上,雷家出售時,是97畝多田加上“河邊溝坎基地約計二十畝零”,不到120畝。到謝氏兄弟出售時,是“水田二段、基址一所、旱土一塊”,共計120畝多。條糧均為2.48兩。
這說明,謝家買下田產后,在21年里,陸續新開墾了接近3畝地。
在房產上,雷家出售時如上所述。到謝氏兄弟出售時,為瓦房五向17間,兩個倉庫,瓦樓門一座等。
相比之下表明,謝家買下雷家的房產后,進行了整改。雷家原有的房產加起來為四向22間,到謝家出售時,為五向17間。這說明謝家對雷家的房屋整改較大,增加了一向,縮減了房間數量。
綜合分析推測,謝家看起來是把房間數量減少了,但提高了房屋質量,其中應該有一定數量的房間是新建的,而且都是瓦房。
雷家和謝家出售這份產業時,都是以田產為主,房產是“捆賣”在地產里的,房產對成交價格的影響基本上很小。所以,在價值上,還是要看土地的價值。忽略銀子的成色問題,從3290兩到4500兩,短短21年里,增長了1210兩。
成都市龍泉驛區檔案局(館)檔案編研負責人胡開全說,這實際上反映了雖然在道光、咸豐時期,由于鴉片貿易導致白銀大量外流,土地價格在回落,白銀在升值,但到了同治年間,土地因為具有稀缺性的本質特征,加上新開墾的土地遠遠不能抵消人口的增長,土地價值又開始上升的社會現實。
張家賣產業
鄰居為何來十人做見證?
嘉慶12年(1807)二月十九日,華陽縣三甲五十一支卓家店村民張宗仁父子,因少銀使用,將家里先前置辦的田地、堰塘、草房、碾坊、廂房等產業賣給馮仁海,價格為九七砝碼的足色紋銀1900兩。
在張家賣這份產業的土地契約中,畫押的人員有29人,其中鄰居見證人多達15人,卓家就占了10人,這是為什么呢?
從土地契約的內容中可以發現,張家這份產業的土地界內,有16座墳。這么多墳墓,難道張家的土地中有一個墳墓群?
其實,不是這樣的。土地契約中雖然沒有寫明張家的土地有多少畝,但寫明了“條糧銀一兩一錢八分整”。
成都市龍泉驛區檔案局(館)檔案編研負責人胡開全說,要計算每兩條糧實際上繳的金額,即土地所有者實際的稅賦額,因為地域不同而千差萬別,是比較麻煩的問題。但是,從龍泉驛區檔案局(館)留存的土地契約中,可以推測出,一兩條糧大約要對應40畝的上田。假如張家的這些土地都是上田,以條糧來換算,張家的土地應該至少有水田45畝多。但實際上,從土地中多達16座墳墓來看,張家的土地肯定算不上全都是上田。農村人對土地金貴得很,哪里舍得把上田用來做墳地,墳地一般會選擇坡地。所以,這樣來看的話,張家的土地至少在50畝以上。
那么,這50畝又是怎樣的一個概念呢?我們用標準足球場來換算,這樣會直觀形象一些。國際足聯規定的標準足球場,長為105米,寬為68米,面積為7140平方米。一畝等于666.67平方米,7140平方米大約為10.7畝。也就是說,張家的土地,面積大約有5個標準足球場那么大。此外,契約中提到“山嶺”“草山”字樣,表明張家的田產不僅有田,也有旱地、山坡等。那些墳墓,應該就在“山嶺”“草山”中。
在16座墳墓中,卓家的墳墓有6座:卓家祖墳,卓淑璝墳,卓淑琨墳,卓淑明墳,卓淑璋母墳,卓家的一座生基墳。
所謂生基墳,是不埋死人的,只埋活人的生辰八字和毛發、指甲、血、衣、鞋等物品,裝在壇內埋入地下,俗稱生墳、壽墳。
生基墳早在唐朝就有相關記載:唐朝著名政治家,與房玄齡、杜如晦、宋璟并稱為唐朝四大賢相的姚崇,在萬安山修筑生基墳,預作壽終的壽墳。這種風氣一直延續到清朝,原因是舊時人們迷信生基墳能催官、增壽、求子、招財,現在已經絕跡了。
2014年8月4日,四川古藺縣一個建筑工地發現了一座明朝古墓,除了墓碑上有奇異的花紋外,墓中沒有金銀玉器,也不見棺木和尸骨,這就是一座生基墳。在張家的土地上,卓家有6座墳墓,舊時人們對逝去的人非常尊重,自然要引起卓家重視。卓家出動10個人來見證張家賣地,也在情理中。
胡開全說,這塊土地位于卓家店,是由卓家先插占再賣出來的,但客家風俗賣地不賣墳,所以留了卓家的很多墳地。
廖家賣產業
背后隱藏了什么秘密?
光緒32年(1906)四月二十六日,簡州義三田一支仰天窩村民廖廷華父子,因需籌錢應用,擬將前一年置辦的山地、房屋、林園、竹木、陰陽二宅基址等賣給陳奕超。價值銅錢300釧(串),由此產生的附加費用等一切喜禮銅錢,共40釧(串)。
所賣草屋院落內外一切附屬土木石竹、釘鐵瓦草以及所賣土地四至以及其內草木、土石、神壇、社廟、古泉、古井、古基、古墓等附屬物,以及“已見未見、已成未成、天覆地載、秋毫之末”一切筆未盡錄之物,均“掃土盡售,毫無提留”。這份清朝滅亡前5年簽訂的土地契約,比較典型又真實地反映了清末的時局以及農村的一些現狀。
首先,相比清朝前期和中期的土地契約,該契約過多地強調杜賣的決絕性。
其次,廖家出售的這份產業,邊界涉及到周、韓、邱、李、董、吳姓等鄰居。
按慣例,在簽訂契約時,都要把涉及到的鄰居請來做見證人。但契約中,卻沒有一個鄰居,只有4個中證人,甚至連最重要的賣主都沒有落名簽字。再次,契約中關于欺詐可能性的警告、避規相當嚴厲,出現了“明抵暗當”、“夫糧不楚”、“內事不明”、“外債當押”、“捏造暗藏不清”等措辭。結合第二、第三個問題,我們不由得要對這份蓋了官府大印的土地契約的合理性和合法性產生懷疑:為什么不把與這次出售產業相關的利益人如鄰居請來做見證?邊界涉及到6家人,難道任何一家都沒時間或不敢來做見證?賣主為何不落名簽字?
這是很反常的事情。鄰居沒來做見證,有可能是賣主不愿請鄰居,契約是悄悄簽訂的。
對賣主廖家來說,這份產業肯定是合法擁有的,之所以要悄悄出售,契約中對賣主那么多苛刻的約束語言,背后一定有說不出的秘密。最大可能,是迫不得已出售,是一次不公平的交易;也有可能是急于脫手而匆匆行事。
契約中,還有一項附加費用,更加復雜詳細,如“老衣脫業、移神下匾、畫字、交界、釧底”等喜禮銅錢均在內。這份產業總價是300串,賣方另出的附加費就有40串,這當然是比較貴的,所以出現另算的情形。
值得注意的是“喜禮”二字。大多數土地契約的賣主是缺錢使用才賣產業,參與買賣的人可以隨喜得禮,這是龍泉驛的客家民俗,無可厚非。但到了清末,這種喜禮變了味,數額巨大。以上種種,折射出的深層次背景,是清末的時政亂象。 封面新聞記者黃勇
特別鳴謝:成都市龍泉驛區檔案局(館)。

想爆料?請登錄《陽光連線》( https://minsheng.iqilu.com/)、撥打新聞熱線0531-66661234或96678,或登錄齊魯網官方微博(@齊魯網)提供新聞線索。齊魯網廣告熱線0531-81695052,誠邀合作伙伴。

農歷小年火車票今日開搶 這些熱門路線車票緊俏!
- 農歷小年火車票今日開搶。今日是元旦假期的第一天,也是2019年農歷“小年”火車票開售的日子。[詳細]
- 中國新聞網 2018-12-30

禁令來了,扶貧活動“人情送禮”當休矣
- 禁令來了,扶貧活動“人情送禮”當休矣。廣東省公安廳派駐羅定市加益鎮合江村幫扶工作隊副隊長羅榮華認為,國務院扶貧辦這個文件很及時,是...[詳細]
- 半月談 2018-12-30
酒桌喪命,酒友擔責 共同飲酒致人身損害該怎么判?
- 共同飲酒致人身損害該怎么判。事情就發生在2015年12月31日晚上,一家酒店的廚師長柴某組織酒店的廚師們在一個餐館聚餐,迎接新年,副廚師長...[詳細]
- 四川在線 2018-12-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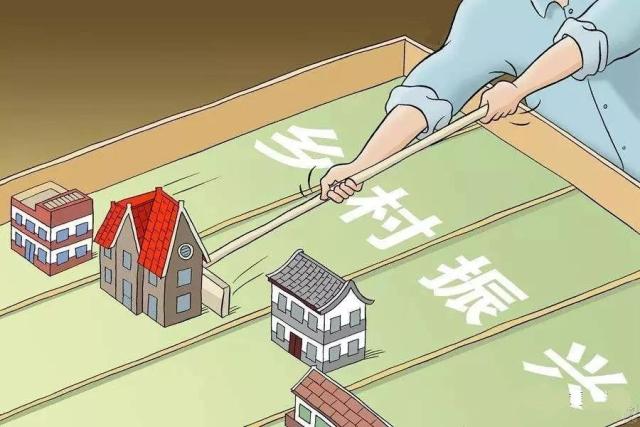
半月談丨亂規劃、被規劃:鄉村振興遭規劃亂象“絆腿”
- 鄉村振興遭規劃亂象“絆腿”。缺乏科學有效的鄉村規劃,正在一些地方讓鄉村振興遭遇“絆腿”。[詳細]
- 半月談 2018-12-29

退役軍人事務部:退役軍人工作領域政策法規建設快速推進
- 退役軍人工作領域政策法規建設快速推進資料圖。中國退役軍人事務部:退役軍人工作領域政策法規建設快速推進中新社北京12月29日電。[詳細]
- 中國新聞網 2018-12-29

中國修改農村土地承包法 “三權分置”實現法制化
- 中國修改農村土地承包法。為落實農村土地所有權承包權經營權“三權分置”,修改后的農村土地承包法規定,承包方承包土地后,享有土地承包經...[詳細]
- 中國新聞網 2018-12-29

最高法:建立知識產權法庭有利于統一裁判標準和尺度
- 建立知識產權法庭有利于統一裁判標準和尺度中新社北京12月29日電。羅東川在發布會上介紹,中國實行兩審終審制,專利類案件過去都是在中級法...[詳細]
- 中國新聞網 2018-12-29

劉少奇故居紀念館無償獲贈經典著作版本填補館藏空白
- 劉少奇故居紀念館無償獲贈經典著作版本填補館藏空白中新網長沙12月29日電。該書前印有劉少奇同志木刻像一幅。[詳細]
- 中國新聞網 2018-12-29

“鴻雁”首發星成功發射 中國全球空間互聯網系統全面啟動
- “鴻雁”首發星成功發射。由中國航天科技集團研制的全球低軌衛星移動通信與空間互聯網系統——“鴻雁”星座的首顆試驗星,29日下午在酒泉衛...[詳細]
- 中國新聞網 2018-12-29

中國將村、居委會任期由三年改為五年
- 中國將村、居委會任期由三年改為五年12月24日,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七次會議舉行全體會。會議聽取全國人大5個專門委員會的代表議案審議...[詳細]
- 中國新聞網 2018-12-29
新年戲曲晚會在京舉行 習近平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出席觀看
- 新年戲曲晚會在京舉行。習近平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出席觀看原標題:新年戲曲晚會在京舉行。[詳細]
- 新華社 2018-12-29
車輛購置稅法公布:稅率為10% 明年起車輛年檢提前?
- 稅率為10%。明年起車輛年檢提前。[詳細]
- 中國新聞網 2018-12-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