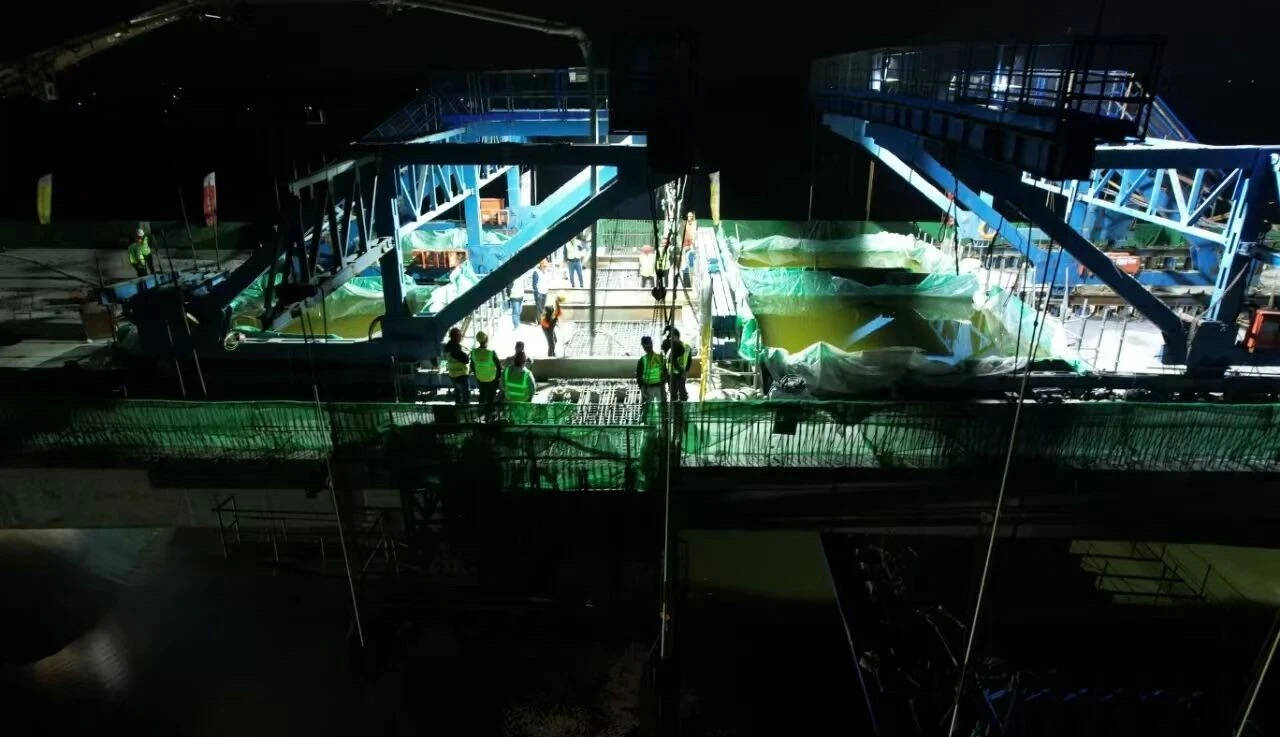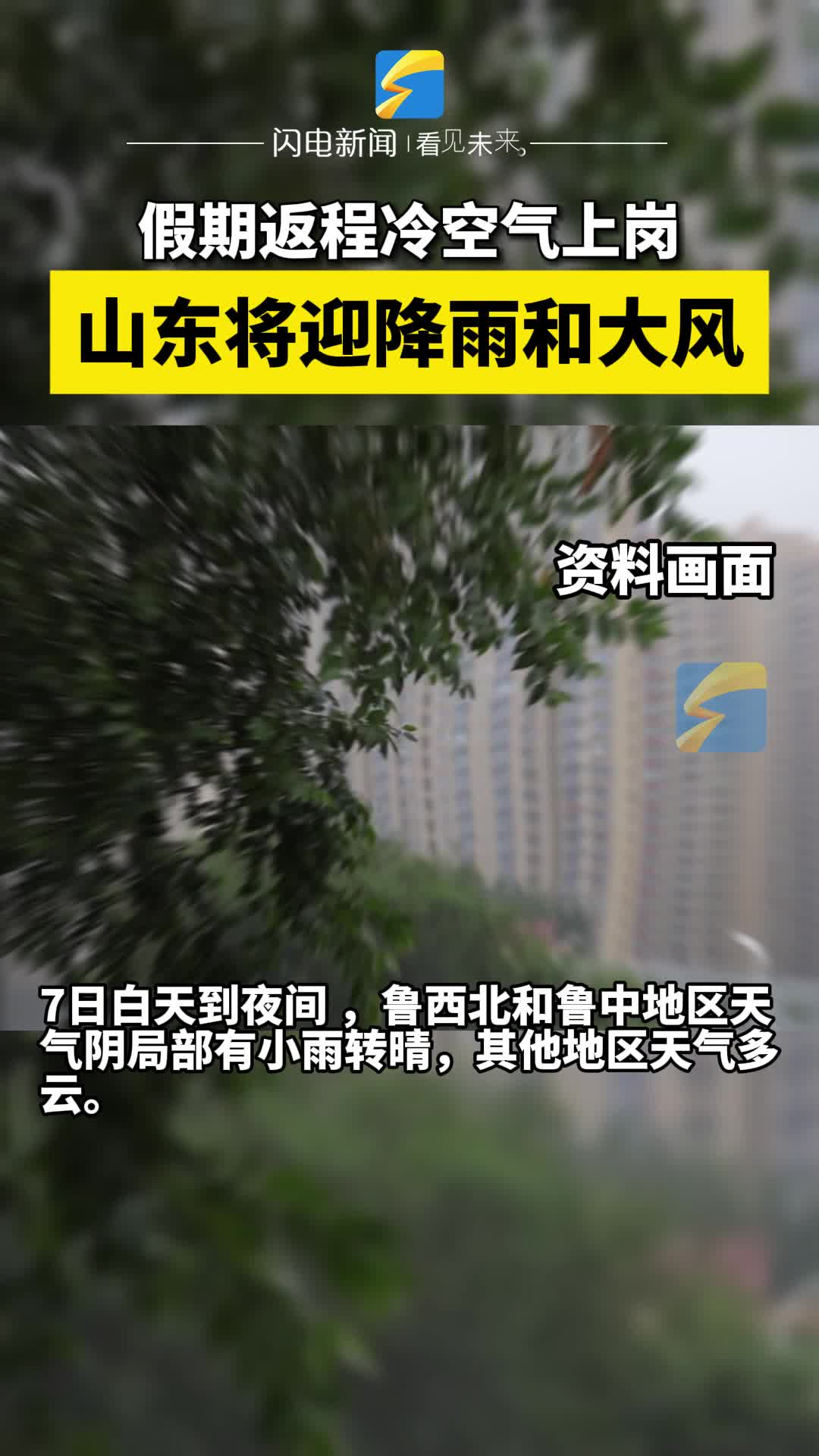2021年中國(guó)(曲阜)國(guó)際孔子文化節(jié)、第七屆尼山世界文明論壇在山東曲阜舉辦。本屆尼山世界文明論壇以“文明對(duì)話與全球合作”主題,邀請(qǐng)來(lái)自世界各國(guó)的專家、學(xué)者共同挖掘古老文明的深邃智慧,共同探討多元文明的相融途徑,呈現(xiàn)了一場(chǎng)人文薈萃的文明盛景、一場(chǎng)百家爭(zhēng)鳴的思想盛宴。
為了更好地展現(xiàn)本屆尼山世界文明論壇的創(chuàng)新理論成果,《理響中國(guó)》特別推出《理響筆記——第七屆尼山世界文明論壇》專欄。今天,《理響筆記》邀請(qǐng)到的是北京大學(xué)、夏威夷大學(xué)教授安樂(lè)哲,他分享的題目是《孔子其人所彰顯的關(guān)系性身份和主體性》。

安樂(lè)哲
北京大學(xué)哲學(xué)系教授
對(duì)以儒家角色倫理為基礎(chǔ)的由關(guān)系構(gòu)成的人的概念的常見(jiàn)關(guān)注之一圍繞身份和主體這 兩個(gè)問(wèn)題展開(kāi),并且在與自由個(gè)人主義所假定的自主、自決式的人的概念相對(duì)比時(shí)變得更為明顯。問(wèn)題在于:焦點(diǎn) - 場(chǎng)域的人觀,能否對(duì)個(gè)人的身份、完整性、自主性提供足夠清 晰的說(shuō)明?回應(yīng)上述關(guān)注的一種可能方式是去反思儒家文本是如何塑造個(gè)人身份和主體性 的,尤其是這兩者又是如何在孔子本人身上反映出來(lái)的。若能這樣做,我們或許可以找 到一種方法——一種訴諸腿與行走之間、身體與具身化生活(embodied living)之間重 要分別的方法,來(lái)替代那種早已陳舊卻仍根深蒂固的“物”(thing)的思維模式。在這 里,我們首先需要區(qū)分兩種主體觀:前者視人為離散的個(gè)體,并以每個(gè)人的意向?yàn)橹敢?活動(dòng)的內(nèi)驅(qū)力;后者既與每個(gè)人密切相關(guān),又推動(dòng)著世界上分散卻又非常集中的人之活動(dòng) (activities)或事件(events)出現(xiàn)。正如行走是雙腿與世界之間的一項(xiàng)重大協(xié)作,我 們不能簡(jiǎn)單地視之為與情景離散或者分離的某物(thing);同樣,人是作為事件(events) 存在于世界的,主體的概念必須具備反映這一事實(shí)的復(fù)雜性。
《論語(yǔ)》中間部分的一些篇章為讀者提供了一系列與孔子生活相關(guān)聯(lián)的真實(shí)畫面,它們與孔子的飲食、行坐、衣著有關(guān),也與孔子在不同的場(chǎng)合如何與人相處有關(guān)。這些不同段落 , 為讀者提供了很多圖像與軼事,將這位模范老師的生活呈現(xiàn)給他那個(gè)時(shí)代的追隨者, 以及代代相傳至今的學(xué)生。也正是在這些核心篇章內(nèi),孔子被描述為有四件他個(gè)人絕不能 容忍的事情——“四毋”,這深刻揭示了孔子的自我認(rèn)識(shí)和他自己的價(jià)值觀:
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孔子杜絕了四種毛病:不憑空臆測(cè),不武斷絕對(duì), 不固執(zhí)拘泥,不自以為是。) 這四個(gè)“毋”加起來(lái)就成為了一個(gè)整體,其積極含義在于:對(duì)孔子而言,過(guò)一種道德 的生活,不僅僅指遵守某種道德教義、依從某些既定規(guī)則。依據(jù)這些嚴(yán)苛的要求,我們可 以推論孔子有他自己所期許的一套總體的、自覺(jué)性高而且詮釋性強(qiáng)的個(gè)人行為習(xí)慣;我們也可以看出孔子畢生所追求的是務(wù)實(shí)的參與(pragmatic engagement)而非抽象的假設(shè) (abstract speculation);開(kāi)放、包容的態(tài)度而非對(duì)終局(finality)的執(zhí)著;靈活的意愿 而非固執(zhí)己見(jiàn);對(duì)他人之需求的敏銳與尊重而非對(duì)一己私利的過(guò)度關(guān)注。這種慣常的、高自覺(jué)性傾向即使不能使人們做到像整個(gè)文化傳統(tǒng)之榜樣的孔子那樣圣賢,也足以激發(fā)對(duì)德 行的追求。
孔子的過(guò)程宇宙論 (process cosmology) 回避了一切強(qiáng)目的論或者唯心主義,它的焦 點(diǎn)是如何更好地活在“當(dāng)下”(very now)。作為一種個(gè)人的處事方式,孔子的“四毋” 將行為與人類經(jīng)驗(yàn)中最直接的東西——關(guān)系——聯(lián)系起來(lái),并且專注于塑造一種習(xí)慣性傾 向,而這種習(xí)慣性傾向在具體應(yīng)對(duì)不斷變化的環(huán)境時(shí)最為有效。雖然我們可以視“四毋” 為一個(gè)整體,認(rèn)為四者相互蘊(yùn)含,但我們?nèi)钥勺穯?wèn):當(dāng)我們單獨(dú)分析這四者時(shí),我們又如何推知孔子自覺(jué)的道德主體?
從記載他生平的文本傳統(tǒng),我們可以看到孔子的思維和行為習(xí)慣;他并不看重迂闊的 抽象原則所提供的表面明晰,而是務(wù)實(shí)地利用更直接、更顯而易見(jiàn)的信息。孔子似乎專注 于思量我們生活中錯(cuò)綜復(fù)雜的角色和事件中那些現(xiàn)成的雜亂無(wú)章而具體的可能性,并依此 行事。孔子之?dāng)⑹碌慕Y(jié)構(gòu)和節(jié)奏在他致力于克己復(fù)禮(即完善自己的各種角色和關(guān)系)的 過(guò)程中充分表現(xiàn)出來(lái)。
在對(duì)人的理解方面,孔子不但抗拒臆測(cè),而且還為我們提供了一套完全自然主義視角 的主體觀,不訴諸于自我的形而上學(xué),也不訴諸任何統(tǒng)一的基礎(chǔ),如靈魂、心靈、自然或 性格。孔子把“人”定義為“仁”,標(biāo)明了一個(gè)在活動(dòng)中而非活動(dòng)前,關(guān)系中而非關(guān)系外 的具有批判意識(shí)、自我意識(shí)的主體。在對(duì)經(jīng)驗(yàn)世界的理解方面,孔子同樣抗拒臆測(cè),反而 引領(lǐng)我們朝著每一天都在發(fā)生的日常事件進(jìn)發(fā),從中尋找我們行為的依據(jù)和理由。孔子給 我們提供的這一個(gè)主體概念,遠(yuǎn)非訴諸于某種簡(jiǎn)單、孤立、高高在上的統(tǒng)一性,對(duì)其最恰 當(dāng)?shù)拿枋鰬?yīng)為——通過(guò)一個(gè)個(gè)生活片段中與孔子相交的同仁、學(xué)生和朋友對(duì)孔子所表現(xiàn)出 的尊敬而聚焦的自覺(jué)的決心。在上述的這些關(guān)系中,“誠(chéng)”在人們的選擇方面似乎擔(dān)當(dāng)了重要角色:孔子并沒(méi)有把自己的意愿強(qiáng)加于其他人身上,他的影響力似乎更多地通過(guò)他對(duì) 周圍人需求的尊重和理解發(fā)揮作用,而這些人的行為也受到了他這一做法的影響。
理解個(gè)人自主性 (personal autonomy) 的傳統(tǒng)方式是自我規(guī)范 (self-legislating):人們 在自己的行為中行使自由和控制權(quán),只要他們受自己個(gè)人意志所支配。在更專業(yè)的康德哲學(xué) 的意義上,自主性是指人的意志自由地服從普遍的道德法則,因?yàn)樗煽陀^理性所決定。與 這些假設(shè)相反,對(duì)由關(guān)系構(gòu)成的而不是離散的人們而言,他們關(guān)系中強(qiáng)制力(coercion) 的缺乏可能成為我們思考關(guān)于自治的這種替代理解的另一種方式。對(duì)孔子而言,自主性似乎 被表達(dá)為人們對(duì)自己的角色和行為有自覺(jué)的決心,對(duì)自己生活中的事件有充分的、創(chuàng)造性的 參與;他們通過(guò)協(xié)商的尊重模式(negotiated patterns of deference)行事,而在這一模 式下,他們能夠在尊重他人利益的同時(shí)找到自己需求的滿足,并在與同伴的關(guān)系中達(dá)至一種 融合的品質(zhì),使他們?cè)谒龅氖虑樯喜皇軓?qiáng)制。這樣的一種自主性,表現(xiàn)為一個(gè)人在行動(dòng)上 的復(fù)雜統(tǒng)一(complex coherence),正如《孟子》所描述的,這就是“配義與道” 。
這種在推測(cè)性假設(shè)上的闕如,立即就體現(xiàn)在以家庭而非以上帝為中心的宗教觀念之中, 這是儒家傳統(tǒng)的標(biāo)志之一。當(dāng)樊遲問(wèn)及“智慧”時(shí),孔子并沒(méi)有嘗試為它下一個(gè)我們從柏 拉圖對(duì)話中熟知的那種通用、正式的定義。孔子僅就樊遲這個(gè)人自身,告誡他要分清事情 的本末輕重:務(wù)民之義,敬鬼神而遠(yuǎn)之,可謂知矣。鑒于亞伯拉罕宗教信仰中普遍存在的推測(cè)性假設(shè),孔子這一與人建立務(wù)實(shí)有效的關(guān)系、 與鬼神保持距離的建議,使得許多評(píng)論家認(rèn)為孔子對(duì)人為培育的宗教信仰的各種要求缺乏 興趣——盡管他也未必厭惡它們。
對(duì)這類評(píng)論家來(lái)說(shuō),孔子在尋求與神靈世界建立親密關(guān) 系這一點(diǎn)上,總是表現(xiàn)得靜默,所以也就清楚地證明了孔子在乎的,是一種世俗的人文主 義(secular humanism)。這種人文主義解讀,在《論語(yǔ)》另一段落,即當(dāng)文本談及孔 子的課程內(nèi)容時(shí)得到強(qiáng)化;或許更重要的是,這一段描述了他的教學(xué)體系所排除的內(nèi)容。 在這一段,我們被告知:雖然孔子樂(lè)于把自己的見(jiàn)解灌注入已被接受并仍在不斷發(fā)展的人 類文化,但他不愿意去推測(cè)人類的未來(lái)命運(yùn),也不愿意去推測(cè)宇宙的將來(lái)會(huì)怎樣演變: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孔子專注于探究我們是誰(shuí),以及我們的文化取得了什么成就,卻似乎不太愿意冒險(xiǎn)猜測(cè)我們和我們的世界可能會(huì)變成什么樣子。
在解釋這些段落時(shí),雖然有些人把孔子思想歸類為去魅的人文主義(disenchanted humanism)。但其實(shí),我們也可以另辟蹊徑進(jìn)行另一種解讀,以與孔子以家庭為中心的 宗教設(shè)想統(tǒng)一起來(lái)。例如,我們可以得出結(jié)論:對(duì)于孔子來(lái)說(shuō),真正的宗教信仰,并不在 于敬畏和祈求遠(yuǎn)古的神祗,而應(yīng)該在鄰里之間建立聯(lián)系。這種另類的宗教信仰表現(xiàn)為一種 共享的、以家庭為中心的精神性(spirituality),這通過(guò)追求一種家庭和社群之間的卓 越生活而實(shí)現(xiàn)。對(duì)孔子來(lái)說(shuō),一個(gè)人的成長(zhǎng)總是圍繞個(gè)人的自修展開(kāi),同時(shí)還應(yīng)致力在緊 密的家庭和社群關(guān)系中不斷地向四周伸延出去,以至于達(dá)到宇宙整體(cosmic totality) 的高度。在那里,有一個(gè)相互滲透的中心和外圍,最自覺(jué)的集中具有最大的延展范圍及影 響力,與此同時(shí),最廣泛的延展又被反射回來(lái)鞏固最集中的東西。更具體來(lái)說(shuō),我們可以 這樣推斷:對(duì)孔子而言,在家庭道德生活中流露的自覺(jué)的尊重、崇敬和感恩,同與對(duì)祖先 的崇敬和一種自然的虔誠(chéng)之表達(dá)相關(guān)聯(lián)的那種靜逸歡愉的精神性兩者之間,具有直接而密 不可分的聯(lián)系。或者更簡(jiǎn)單地說(shuō),這種儒家的宗教信仰只不過(guò)是一種宇宙歸屬感,是由我 們?cè)谧钪苯印⒆钣H密的關(guān)系中獲得的價(jià)值感所激發(fā)的。
如果拉丁文“ 宗教”(religare) 一詞的本義確實(shí)意味著“ 緊密結(jié)合”(to bind tightly),那么,禮似乎就是理解這種以家庭為中心的宗教的關(guān)鍵詞,因?yàn)樗且环N社會(huì) 語(yǔ)法(social grammar),能夠在社會(huì)結(jié)構(gòu)中產(chǎn)生有意義的聯(lián)系并增強(qiáng)其強(qiáng)韌度。“禮”, 始于對(duì)家庭和宗族的儀式化奉獻(xiàn),然后擴(kuò)展到社群,并同時(shí)把眾人的角色以及他們之間的 關(guān)系神圣化。在這一解讀下,傳承至今的傳統(tǒng)春節(jié)應(yīng)被視為一個(gè)意義深遠(yuǎn)的宗教事件。在 這一人類歷史上規(guī)模最大的人口遷移中,我們見(jiàn)證了主要移民城市人口大量向外流動(dòng)的現(xiàn) 象。在中國(guó),幾乎每個(gè)人都會(huì)用盡一切可用的交通方式在春節(jié)期間返回家鄉(xiāng),進(jìn)行持續(xù)一 段時(shí)期的莊重的道德“再創(chuàng)造”(re-creation)。這一再創(chuàng)造活動(dòng)由一個(gè)終其一生都受 到道德教育的熏陶、十分尊敬培育了自己的家族、長(zhǎng)輩、老師以及社群的人群參與,并且 他們會(huì)把自己的“老家”視為判別自己個(gè)人身份的一項(xiàng)主要決定因素。本著這種對(duì)家庭的 崇敬,他們回歸自己的“根”,去續(xù)存他們最親密的關(guān)系,在幾周后蓄積了足夠的力量, 又返回城市里去工作,如此這般,年復(fù)一年。
唐君毅先生將這一充分體現(xiàn)了以家庭而非上帝為中心的宗教信仰的早期中國(guó)天道觀 (cosmology)概括為“性即天道觀”。這一主張承認(rèn)了這樣一個(gè)事實(shí),即我們正在成為 什么樣的人這件事從根本上被嵌入到我們無(wú)限的敘事中,因此,只能通過(guò)考慮我們?nèi)P的 情境化關(guān)系來(lái)全息地理解之。這種對(duì)焦點(diǎn) - 場(chǎng)域主體性(focus-field agency)的理解, 要求人們從最遠(yuǎn)的外圍場(chǎng)域走近焦點(diǎn)然后進(jìn)入中心點(diǎn),同時(shí)又要從整體到特殊,從與我們 無(wú)關(guān)痛癢的各種因素走向與我們最相關(guān)的各項(xiàng)細(xì)節(jié)。這種焦點(diǎn) - 場(chǎng)域主體描述了一個(gè)人的 自我意識(shí)顯現(xiàn)為整體中或多或少有意義的決心的中心。孔子本身就是一個(gè)敘事場(chǎng)域,他的 后人可以在《論語(yǔ)》以及其他經(jīng)典文獻(xiàn)中看到這些故事。后學(xué)通過(guò)在孔子的大小故事里面尋找靈感來(lái)塑造自己獨(dú)特的人格與行為習(xí)慣,而把孔子的敘事變成他們自己生活的一部分。
子絕四之二——“毋必”(不武斷絕對(duì))。這樣避免將固定的、終極的東西作為命令 或普遍法則是基于他對(duì)變化和新奇的基本尊重。它反映了孔子對(duì)置身于“生生不已”這個(gè) 宇宙法則之中的人類生命的開(kāi)放式復(fù)雜性(open-ended complexities)的一種覺(jué)悟。“生 生不已”四字出自《周易》,有連續(xù)不斷并且不可逆轉(zhuǎn)地在變動(dòng)的深邃意涵。在《周易》 的其他段落,這一生生的過(guò)程被明確表述為“天地之大德曰生”。這表明我們的出身、成 長(zhǎng)、生活都在情境化的、不斷發(fā)展的自然、社會(huì)和文化關(guān)系中展開(kāi),在這一背景下,自我 意識(shí)的成長(zhǎng)本身就是宇宙道德的實(shí)質(zhì)。在這一個(gè)過(guò)程中,主體感首先出現(xiàn)在我們?cè)诓粩嗾?開(kāi)的個(gè)人敘事中,目的明確、深思熟慮地?fù)?dān)負(fù)起至關(guān)重要的、常與人協(xié)作的角色時(shí)。焦點(diǎn) - 場(chǎng)域的、關(guān)系性的主體性的這一典型特征,要求我們不僅要對(duì)這些角色的持續(xù)成長(zhǎng)保持不 懈關(guān)注,還要具備足夠的道德想象力,去意識(shí)到并且應(yīng)對(duì)不斷變化的外在環(huán)境。不可化約 的復(fù)雜的人是生動(dòng)而活躍的,在不斷地尊重他人、與他人協(xié)作的過(guò)程中, 他們必須保持 隨機(jī)應(yīng)變、知錯(cuò)能改以及樂(lè)于助人。對(duì)他們來(lái)說(shuō),這一切既沒(méi)有終局也沒(méi)有結(jié)束。
與此相關(guān)的是子絕四之三——“毋固”(不固執(zhí)拘泥)。這一種靈活性,為明于自省 的人所必備,因?yàn)樗麄兠翡J地意識(shí)到人類經(jīng)驗(yàn)交易、聯(lián)合的性質(zhì),并坦然接受在周圍其他 人的域境內(nèi)自己身份之多重性,是多變而又確定的焦點(diǎn)。這種焦點(diǎn) - 場(chǎng)域的主體,必須被 理解為在他們重要的關(guān)系模式之中自覺(jué)地去塑造或接受塑造的、不可化約的交易性的主體。 根本而言,這種主體性只能通過(guò)已然確立的認(rèn)同和順從習(xí)慣而議定。也就是說(shuō),雖然這種 行動(dòng)在受到過(guò)去影響的意義上必然是被動(dòng)的,即總是“承受”著他人的行動(dòng),但它同時(shí)也 必須在自覺(jué)性、靈活性、目的性、前瞻性幾個(gè)方面找到適當(dāng)?shù)钠胶狻:?jiǎn)而言之,我們只有 在定義我們身份的活動(dòng)中靈活反應(yīng),才能過(guò)一種道德上負(fù)責(zé)任的生活。
子絕四之四——“毋我”(不自以為是)。具有高度自覺(jué)意識(shí)的主體有不可化約的社 會(huì)性,不能以自我為中心。隨著通過(guò)在關(guān)聯(lián)中塑造了他們的符號(hào)學(xué)過(guò)程、符號(hào)學(xué)能力而逐 漸適應(yīng)于一種文化(enculturated),這些焦點(diǎn) - 場(chǎng)域的主體從與他人的“內(nèi)在”主觀關(guān) 系(“intra-”subjective relations)中發(fā)展出自己的一套自我反思和反省意識(shí)。這些既 是精神的又是極度物質(zhì)的物活性主體(hylozoistic agents),必然以他們散漫卻活力充 沛的血肉之軀,演活他們生命之中的多種角色。但是,當(dāng)他們努力地在變化著的同樣有機(jī) 的身體和社會(huì)關(guān)系(equally organic physical and social relations)結(jié)構(gòu)中實(shí)現(xiàn)一己的 一致性時(shí),他們的身體就像形成了多孔薄膜那樣,不斷地將經(jīng)驗(yàn)內(nèi)化為他們發(fā)展著的身份的一部分。
這些焦點(diǎn) - 場(chǎng)域的主體必須施展他們通過(guò)學(xué)習(xí)得來(lái)的能力以應(yīng)對(duì)所處環(huán)境,而同時(shí)在與 其他人共享的活動(dòng)之中,非強(qiáng)制地展現(xiàn)出一種由關(guān)系定義的自主性。這種自主性是這些環(huán)境 當(dāng)中合作關(guān)系的最直接結(jié)果——一個(gè)合作網(wǎng)絡(luò)的價(jià)值和目的變成與每個(gè)協(xié)作者自己的相一致。
盡管儒家角色倫理學(xué)是從一個(gè)獨(dú)特的視角考察道德生活,有著自己的一套特定、專門的詞匯,但在另一種哲學(xué)背景下更好地理解這一學(xué)說(shuō),并更有效地與當(dāng)代西方哲學(xué)家溝通 的另一種方法也許是問(wèn)這樣一個(gè)問(wèn)題:對(duì)于當(dāng)代自由主義在討論倫理學(xué)理論常用的專業(yè)術(shù) 語(yǔ),例如“自主”、“選擇”,我們能否將之重構(gòu),然后用來(lái)有效地解釋儒家角色倫理學(xué)呢?
自主性(autonomy)一詞在個(gè)人主義的意義上是“Gk autós”自我 +“Gk nomos”法則,字面的意思為:對(duì)自己發(fā)號(hào)施令的人,或自我立法的人。在儒家角色倫理 學(xué)里,我們不能把“自主的人”理解為獨(dú)立、理性的行動(dòng)者;也不能把“選擇”理解為人 們可以在的他們?nèi)粘I畎l(fā)生的事情之中,以獨(dú)立行動(dòng)者的身份進(jìn)行自由選擇。在儒家的 傳統(tǒng)內(nèi),擁有自主性的行動(dòng)者的選擇,一定指的是受關(guān)系制約并且徹底嵌入其中的人,通 過(guò)投身他們自己特定敘事中的角色的特性而表達(dá)自己的偏好。我們所理解的“關(guān)系性自主” (relational autonomy)并不是指那些對(duì)自己特殊、獨(dú)立的行動(dòng)擁有操控權(quán)的個(gè)體,而 是指那些有自我意識(shí)但又有不可化約社會(huì)性的主體,他們通過(guò)在持續(xù)的交往中相互適應(yīng), 能夠在非強(qiáng)制的情形下行動(dòng)。同樣地,我們所說(shuō)的“抉擇”(thick choices)并不是指 離散個(gè)體不受他人影響、不考慮他人利益地行使自己的自由時(shí),所作出的碎片式重大決定, 而是指具有批判性自我意識(shí)的社會(huì)性主體,隨著時(shí)間的推移,表明了他對(duì)自己的角色和關(guān) 系中的某種行為模式一以貫之的堅(jiān)持。
傳統(tǒng)上,自由理論中的“自主”是指自我管治(self-governance)意義上的獨(dú)立自 主,由一個(gè)被認(rèn)為是離散、排他的自我開(kāi)始。可以說(shuō),這種個(gè)體離散性的概念僅僅是一種 功能性的抽象,并且有時(shí)候所謂絕對(duì)自主對(duì)這一點(diǎn)的聲稱其實(shí)是一種誤導(dǎo)性的,卻仍然具 有強(qiáng)大影響力的虛構(gòu)。事實(shí)上,假如關(guān)聯(lián)生活(associated living)是實(shí)情的話,我們表 面的離散,就不是一個(gè)初始條件,同時(shí)也不會(huì)排斥別人。相反,我們會(huì)變得獨(dú)特甚至出色 恰是因我們一直以來(lái)能夠與人相處而具有的特性。儒家的人觀為我們提供了關(guān)于獨(dú)特的、 相互依存的人的另一種動(dòng)名詞的概念,對(duì)他們來(lái)說(shuō),他們的關(guān)系性、獨(dú)特性、社會(huì)性,正 是他們個(gè)性化(individuation)的來(lái)源及表現(xiàn)。而且,對(duì)他們來(lái)說(shuō),這種個(gè)性化——獨(dú)特、 堅(jiān)定的特質(zhì)——非但沒(méi)有拒人于千里之弊,反而是通過(guò)他們?cè)跇?gòu)成自己的關(guān)系模式中所達(dá) 到的水平高低來(lái)衡量的。自覺(jué)的、關(guān)系性的自主所描述的是目的明確、非強(qiáng)制的活動(dòng),因 為這些活動(dòng)在我們的角色和關(guān)系中實(shí)現(xiàn)圓滿。有批判性自我意識(shí)的、不可化約的社會(huì)性的 主體的抉擇(thick choices)描述了這些主體在其生活角色中所具有的決心和承諾。
由關(guān)系構(gòu)成的人與他人相互依賴,彼此沒(méi)有特定界限,因此在任何情況下,作為“自 我管治”的自主都需要一個(gè)集中但在程度上分散的個(gè)人身份,以及在交際中,它必須將所有相關(guān)的利益都作為其自主特性的組成部分。對(duì)以上這種相互依存的自我來(lái)說(shuō),關(guān)系性的自主要根據(jù)彼此之間的關(guān)聯(lián)做出協(xié)調(diào),即協(xié)調(diào)人與人之間的特殊差異,以期在大家共享的明智做法中實(shí)現(xiàn)有意義的多樣性。這樣的一種關(guān)系性自主定義,跟一些表面上的獨(dú)立自主的選擇的說(shuō)法大相徑庭;它就是一種功能,在自愿尊重他人利益的前提下來(lái)達(dá)到自己的合 理目的,從而能夠在常見(jiàn)的共同活動(dòng)中把強(qiáng)制減少。事實(shí)上,那些被視為模范的人,他們的自主性比其他人更強(qiáng),甚至變成了啟迪別人的榜樣——他們能夠吸引人群,并且通過(guò)獲得大家尊重的方式,他們的價(jià)值觀影響和塑造了群體行為。以圣雄甘地、馬丁·路德·金、納爾遜·曼德拉三人的模范人格故事為例來(lái)說(shuō),他們都具備這么一種關(guān)系性自主,并且通 過(guò)作為榜樣的作用,影響了一代又一代的人,并且已經(jīng)造成了定義我們這個(gè)時(shí)代的價(jià)值觀的持續(xù)巨變。通過(guò)尊重他們所代表的東西,以及追隨他們的價(jià)值觀,我們所有人都與他們每一個(gè)人的共同身份(corporate identities)關(guān)聯(lián)起來(lái)。
這里要說(shuō)明的一點(diǎn)是,本構(gòu)關(guān)系(constitutive relations)原則并不會(huì)剝奪人們各自的主體性或者選擇權(quán),而只是要求我們以與關(guān)聯(lián)性生活的經(jīng)驗(yàn)事實(shí)相符合的方 式重新思考我們所熟悉的如自主、選擇這樣的術(shù)語(yǔ)。鑒于基礎(chǔ)個(gè)人主義 (foundational individualism) 作為一種存在已久的常識(shí)性看法所具有的巨大吸引力,提及由關(guān)系構(gòu)成的 人的概念,會(huì)常常被誤解為要向我們提供一種被大大弱化的個(gè)人身份感。然而,一個(gè)強(qiáng)有力的例子可以證明,在關(guān)系上建立的人觀不但沒(méi)有損害作為個(gè)人自主性表述而受到高度評(píng) 價(jià)的獨(dú)特身份,實(shí)際上反而提升了它。例如,在希臘唯心主義人類范式中,個(gè)體身份是外部關(guān)聯(lián)、個(gè)體分散式的,每個(gè)個(gè)體都被賦予一些相同的特征(eidos)。在這樣的一個(gè)范式下, 人被視為本質(zhì)上是同一的,只是偶然會(huì)有一點(diǎn)分別。在這個(gè)模型中,個(gè)人身份只能帶有一 種相對(duì)殘缺的獨(dú)特感。相比之下,本構(gòu)關(guān)系之假設(shè)——我們每一個(gè)人都是一個(gè)非凡、獨(dú)特、 不可替代的,是且僅是我們自己的關(guān)系矩陣——中的一個(gè)學(xué)說(shuō)即是一種徹底嵌入式的人的模型,這一模型反而將那些可被歸于個(gè)人的特殊性和獨(dú)特性放大了。
此外,通過(guò)說(shuō)明個(gè)體身份自覺(jué)、專注、目的明確、有決心,并且同時(shí)在重要程度上擴(kuò)散在我們的關(guān)系中,角色倫理學(xué)在生活的事件當(dāng)中定位人,從而提供了一種經(jīng)驗(yàn)上更有說(shuō)服力的人的主體性概念。雖然我們焦點(diǎn)身份的獨(dú)特性由這樣的決心而得到確定,但這種獨(dú)特性與我們對(duì)他人的意義相關(guān),并且依賴于此。在我作為母親的兒子這個(gè)角色中,我一直 以來(lái)的身份與行為必然受到我對(duì)親愛(ài)的母親的感情的尊重的影響。個(gè)人身份當(dāng)然是特殊和獨(dú)特的,但同時(shí)它也是具有多種意義的,其中包含了多段錯(cuò)綜復(fù)雜的關(guān)系,所以是包括而 不是排除我們周邊的其他人。如此理解我們的角色身份,那么它雖然是持久的,但也在不 斷地變化;雖然非常自覺(jué)地富有目的性,但同時(shí)也非常包容和圓通;雖然出自主觀個(gè)人, 但同時(shí)也尊重并關(guān)心其他人。
當(dāng)我們轉(zhuǎn)向儒家文本去證實(shí)這種關(guān)系性的自主而非個(gè)人性的自主,以及一以貫之的抉 擇而非碎片化的選擇,我們或者可以套用黃百銳從《論語(yǔ)》中引用的一段話作為說(shuō)明。 黃百銳就是以它為例發(fā)展出他自己稱之為“關(guān)系性的、自主的自我”(relational and autonomous selves)的微妙概念:
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黃百銳對(duì)這段話的理解是:孔子比大多數(shù)人更“自主”,因?yàn)樽鳛橐粋€(gè)模范人物, 他是自己行為的唯一控制者,能夠堅(jiān)持一種理想的整體特質(zhì)——“義”,而不受被他影 響的人的影響。這里表現(xiàn)出來(lái)的正義感,使得他能夠不受那些在特定環(huán)境下由特定的人 觸發(fā)的特定情境特征的影響。用黃百銳自己的話說(shuō)就是:“似乎貴族階層的部分成就就 在于這種保持道德卓越的能力,無(wú)論他們走到哪里,和誰(shuí)一起生活,他們都能對(duì)他人施 加影響。”
我們隨即就會(huì)想到一些也許能夠支持黃百銳上述說(shuō)法的《論語(yǔ)》文本佐證。舉例來(lái)說(shuō): 季康子問(wèn)政于孔子曰:“如殺無(wú)道,以就有道,何如?” 之風(fēng),必偃。” 孔子對(duì)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fēng),小人之德草。草上我們也許可以從這段話中得出與黃百銳的解讀相關(guān)的一個(gè)類比:孔子是明辨是非的典 范,而東夷是蒙昧的不辨是非的人,這些人將不得不俯首于孔子的正面影響之“義”。
孔子在這一對(duì)話中想要表達(dá)什么?首先,身為國(guó)相兼三家之首的季康子,被孔子視為 篡奪魯國(guó)王權(quán)的人。而從這個(gè)段落以及其他幾個(gè)段落,我們知道孔子把這個(gè)篡權(quán)者看作是 一個(gè)無(wú)能管治國(guó)家的人。季康子想要把殺死一些自己的人民作為管治國(guó)家的方法這一事實(shí) 也遭到孔子譴責(zé)。對(duì)孔子來(lái)說(shuō),有效的管治,取決于統(tǒng)治者在多大程度上是他們用以教化 人民的價(jià)值觀的典范。但這些價(jià)值的來(lái)源又是什么?“善”在這段話中被解釋成為統(tǒng)治者 努力達(dá)至行為上的“善”(good),而不是單從人所固有的某種先天的或更高層次的“善” (goodness)衍生出來(lái)的某種優(yōu)越的品格特征;也不是某種通過(guò)指導(dǎo)一個(gè)人的行為而得 到踐行的“善”的一般原則。也就是說(shuō),道德成長(zhǎng)意義上的“善”始于連續(xù)敘事中散漫的 關(guān)系性活動(dòng)。只有這樣,它才能充當(dāng)對(duì)一個(gè)人或一個(gè)行為的一般描述。“善”是通過(guò)相互“聯(lián)系”(relating)和有效溝通來(lái)發(fā)展我們的關(guān)系并使它們變得“有意義”(meaningful) 的社交活動(dòng)。要想真正做好我們所做的事情,并且使得這樣的行為對(duì)我們的同伴也是善的, 需要尊敬和尊重。
一切行為那種不可化約的關(guān)系性質(zhì),以及“善”作為一種特性的事實(shí),被理解為是在 關(guān)系本身中得到實(shí)現(xiàn),而不是作為屬于模范者的某種品質(zhì)。以上這一點(diǎn),在《論語(yǔ)》另外 一個(gè)相關(guān)段落中得到明確闡釋:即文明人與野蠻人之間的區(qū)別,與追求行為完滿的人們所 要求的行為質(zhì)量無(wú)關(guān)。無(wú)論是與家人、公眾,還是與昔日的“野蠻人”打交道,完美的行 為都需要真誠(chéng)的尊重、尊敬和盡心:
樊遲問(wèn)仁。子曰:“居處恭,執(zhí)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論語(yǔ)》中這段提到德風(fēng)草偃比喻的話,在《孟子》中也有出現(xiàn)。就一位國(guó)君之死, 孟子向其儲(chǔ)子提出忠告,建議后者遵從孔子的訓(xùn)示,為朝廷設(shè)立一套新的守喪三年的規(guī)矩。 同樣,這里的傳達(dá)的信息一定是:統(tǒng)治者必須成為影響人民做出改變的榜樣。但要指出的 重要一點(diǎn)是,模范人物的影響,來(lái)自他們與其他人交往時(shí)的尊敬和尊重,因?yàn)檫@種態(tài)度, 本身就是他們?yōu)椤吧啤焙妥觥霸谝欢ㄇ闆r下最適當(dāng)?shù)氖虑椤保x)的源泉。
孟子對(duì)這位世子的勸告,始于世子自覺(jué)地認(rèn)識(shí)到自己過(guò)去荒廢學(xué)業(yè)而沒(méi)有受到朝廷官 員和親人的重視。因此,作為新即位的國(guó)王他將難以獲得他們?cè)趪?guó)家事務(wù)上的支持。世子 遵從孟子的勸告,注重自己的品格,故此能夠提升和完善自己的行為,給人民樹(shù)立榜樣。 通過(guò)這樣做,他贏得了朝廷的尊重并且能夠改變大臣們的行為。如此一來(lái),這種改變是并 行的:世子的品格,因?yàn)槿嗣竦钠谕玫礁纳疲娜嗣瘢惨驗(yàn)樗F(xiàn)在的模范行為而相應(yīng)得到改變。
下面我們按照解讀《孟子》中這一段話的方式來(lái)解讀《論語(yǔ)》中孔子想要與東夷一起生活的段落。對(duì)孔子來(lái)說(shuō),“義”有“做最合適的事情”的意思,這當(dāng)然也是他 在這種情況下(或者在任何其他情況下),將作為最終決定因素而援引的標(biāo)準(zhǔn)。不過(guò), 對(duì)孔子而言,“義”的觀念又肯定不是某種遙不可及的、前置的原則,憑借著明示的客觀性和普遍性,可以放諸四海而皆準(zhǔn)。相反,孔子認(rèn)為:與夷人一起生活,那些渴 望成為榜樣的人和夷人一樣,通過(guò)相互遷就以及在人際關(guān)系中追求最適當(dāng)?shù)年P(guān)系,彼 此都會(huì)變得越來(lái)越“意義重大”(significant,義 ) 。而在這個(gè)共同的敘事中,孔子 和“夷人”的身份都會(huì)發(fā)生重大轉(zhuǎn)變。考慮到由關(guān)系構(gòu)成的人,黃百銳所說(shuō)的“理想 的整體特質(zhì)”其實(shí)就是通過(guò)多數(shù)人的利益和典范人物的行為關(guān)聯(lián)起來(lái)而實(shí)現(xiàn)的。這樣, 由孔子行動(dòng)隨之而來(lái)的“行而宜之”(義),就會(huì)符合所有相關(guān)方(即孔子和夷人) 的利益。正是這種在多樣性中實(shí)現(xiàn)的共享和諧(一多不分)構(gòu)成了孔子的關(guān)系性自主。夷人受到啟迪,向孔子學(xué)習(xí)并以孔子為榜樣,他們的行為肯定會(huì)有所改變,使他們能 夠戒除任何陋習(xí)。與此同時(shí),隨著夷人在他的影響下行為既得到道德上的提升又保留 了自身獨(dú)特性,孔子也將擴(kuò)大自己的影響范圍。重要的是,這段話并非期許單方面將 一個(gè)既定的標(biāo)準(zhǔn)強(qiáng)加于東夷,孔子與東夷必須以一種并行關(guān)系在攜手合作中相互適應(yīng)、 共同成長(zhǎng)。
從孔子的角度出發(fā),通過(guò)接觸和學(xué)習(xí)另一種文化,他對(duì)“義”的理解(即什么是適當(dāng) 的和有意義的)會(huì)變得更加豐富。事實(shí)上,當(dāng)孔子的學(xué)說(shuō)被接受并且適應(yīng)于新人群的不同思維方式和生活方式,孔子本人的地位和影響也將得到價(jià)值提升。榜樣當(dāng)然會(huì)激勵(lì)那些效 仿他們的人,可是如果沒(méi)有這樣的效仿,他們也不能成為模范榜樣,并且效仿者對(duì)榜樣的 尊敬,也會(huì)引起這些榜樣自身的重要變化。
作為理解上面這個(gè)段落的一種具體方式,我們或許可以思考儒家文化對(duì)“東夷”—— 即朝鮮、日本、越南這三個(gè)東亞民族歷史的延伸。這種文化價(jià)值觀與制度不是通過(guò)武力或 者占領(lǐng)強(qiáng)加給其他東亞國(guó)家的。在過(guò)去的幾個(gè)世紀(jì)以來(lái),儒家文化一直都在以不同方式在 不同程度上,被這些不同的人群自覺(jué)接受和使用。而且,在此一轉(zhuǎn)變過(guò)程中,被轉(zhuǎn)化的不 僅僅是這三者,而其實(shí)牽涉到全部的四個(gè)漢文化傳統(tǒng)。韓國(guó)、日本和越南的獨(dú)特文化,以 及中國(guó)儒家文化自身的本質(zhì),全部都因?yàn)檫@一全息的焦點(diǎn) - 場(chǎng)域過(guò)程而變得不同并且更加 豐富。在這種全息的焦點(diǎn)-場(chǎng)域過(guò)程中,每種文化都與其他文化相互關(guān)連。在這種模式下, 自主并不是一個(gè)所謂“正確”的范本通過(guò)單方面超越其他文化影響并將秩序強(qiáng)加于他人, 從而控制他人。相反,關(guān)系性的自主需要同時(shí)結(jié)合非強(qiáng)制性的解決方案和回應(yīng)性的尊重。 這是一個(gè)機(jī)會(huì),讓身處關(guān)系里的所有各方,都可以以自己獨(dú)特的方式,為不斷演變的文化 傳統(tǒng)作出貢獻(xiàn);這種傳統(tǒng),同時(shí)也是“一多不分”的。如此一來(lái),所有各方都在這個(gè)多邊進(jìn)程中得到轉(zhuǎn)化。
在當(dāng)前歷史時(shí)刻,中國(guó)、韓國(guó)、日本和越南這四種獨(dú)特的儒家傳統(tǒng)似乎都處于上升階段,鑒于他們所信奉的儒家價(jià)值觀,他們應(yīng)逐漸成為當(dāng)下不停變動(dòng)的世界文化秩序的重要資源。本來(lái),儒家作為東亞地區(qū)的一種整體性現(xiàn)象,對(duì)當(dāng)下這個(gè)不停變動(dòng)的世界文化秩序的塑造,應(yīng)該是很有作為的,但隨著他們自身關(guān)系的弱化,他們對(duì)這種新文化秩序產(chǎn)生影響的可能性,就在很大程度上被削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