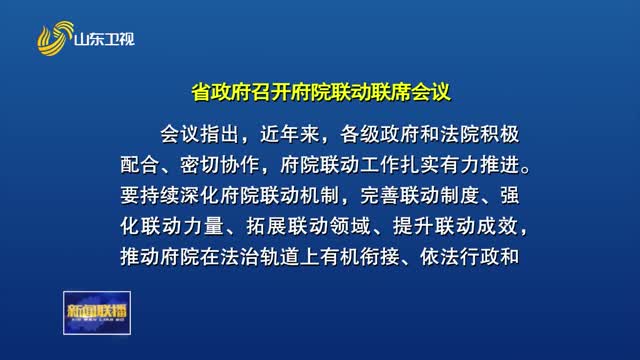青島紅瓦
來源:青島晚報
2025-06-17 09:05:06
原標題:青島紅瓦
來源:青島晚報
原標題:青島紅瓦
來源:青島晚報
周常溫
青島的紅瓦,排布在起伏的山坡上,宛如一片凝固的火焰。這紅色不甚鮮艷,倒顯出幾分沉著,大約是被海風吹拂久了,顏色便也學會了隱忍。
紅瓦的來歷,與德國人頗有些干系。1897年,德人強租膠州灣,便決意將青島建成“東亞明珠”。他們帶來圖紙、機械,還有那固執的日耳曼審美。德國人做事向來認真,連屋頂也不肯馬虎。他們引入德國的制瓦技術,在青島設窯燒制。這便是大窯溝紅瓦的起源了。
大窯溝的地勢低洼,土質卻極適宜制瓦。德國技師指揮著中國工人掘土、和泥、制坯,然后煅燒。火焰在窯內舞蹈三日,泥土便脫胎換骨,成了堅硬的紅瓦。初時,瓦色鮮紅如血,經年累月后,漸漸沉淀為暗紅,倒像是被時光咀嚼過一般。
我在老城區的街巷中信步,抬頭便見岧岧屋頂上那些紅瓦排列如魚鱗,在陽光下泛著微光。海霧漫來時,紅瓦便隱在朦朧中,只露出模糊的輪廓,仿佛無數蹲伏的獸脊。這景象頗有些神秘,使人不覺駐足凝視。
德國人的紅瓦屋頂,坡度很陡,據說是為了抵御雨雪。他們又在檐下設計精巧的排水系統,將雨水引向地面。每逢下雨,雨水從紅瓦上奔流匯入檐槽,再通過水管瀉下,那聲音清脆悅耳,竟像是某種奇特的樂器。我常想,這大約便是建筑與自然的私語吧。
紅瓦的顏色是會唱歌的。晴日里,它是明亮的男高音;陰天時,又轉為低沉的男中音;而到了雨后,濕潤的紅瓦便成了溫柔的女聲,輕輕哼著古老的調子。這種通感,非細心人不能體會。德國人當年燒制這些紅瓦時,可曾想到它們會在百年后,成為一個異鄉人眼中的詩意?
青島的紅瓦與綠樹相映成趣。德國人喜植懸鈴木,其葉大如手掌,春夏翠綠,秋日金黃。紅瓦從綠葉間探出頭來,宛如害羞的少女面頰。海風掠過時,樹葉沙沙作響,紅瓦卻沉默不語,只靜靜聆聽。這紅與綠的對話,已持續了一個多世紀。“青山,碧海,紅瓦,綠樹。”康南海提煉青島色彩的八個字,久已懸于旅行者的記憶之中。
大窯溝的紅瓦工廠早已不存,原址上矗立起了商場與住宅。唯有那些老建筑上的紅瓦,仍在訴說著往事。我見過工人修繕屋頂,他們將破損的舊瓦輕輕取下,換上新燒制的紅瓦。新瓦顏色鮮艷,與周圍的舊瓦格格不入,顯得頗為突兀。但過不了幾年,風吹日曬,新瓦也會變得沉穩,與它的前輩們融為一體。時間是最公正的調色師。
德國人在青島待了17年。他們留下的紅瓦卻比政治更長久。這些紅瓦見證了殖民者的來去,見證了城市的發展,卻始終保持著沉默的姿態。我想,紅瓦或許是睿智的,它們知道一切喧囂終將過去,唯有美可以留存。
冬日,雪落在紅瓦上,紅白相映,分外鮮明。雪融化時,水珠沿著瓦楞滴落,節奏舒緩,好似自然的鐘表。我曾在這樣的午后,坐在閣樓窗前,看紅瓦上的雪漸漸消融,露出原本的顏色。那紅色在雪的映襯下,顯得格外溫暖,仿佛能驅散整個冬天的寒意。
紅瓦也是有記憶的。它們記得德國技師的嚴謹,記得中國工人的汗水,記得戰火中的震顫,也記得和平年代的安寧。每一片紅瓦都是一頁歷史,只是無人能夠解讀。
如今青島的老城區已成為保護對象,那些紅瓦屋頂被列為文化遺產。游客們舉著相機拍攝,贊嘆這“異國風情”。他們可曾想過,美有時是帶著傷痕的,就像這些紅瓦,雖然美麗,卻是殖民時期的產物。
夏日黃昏,我常常登臨信號山,俯瞰青島老城。夕陽西下,紅瓦被染成金紅色,整座城市仿佛在燃燒。這景象壯麗而略帶憂傷。紅瓦之下,是無數平凡的人生;紅瓦之上,是永遠流動的天空。
青島紅瓦,是凝固的音樂,是可見的氣味,是沉默的講述者。
本版主持人 賈小飛
想爆料?請登錄《陽光連線》( https://minsheng.iqilu.com/)、撥打新聞熱線0531-66661234或96678,或登錄齊魯網官方微博(@齊魯網)提供新聞線索。齊魯網廣告熱線0531-81695052,誠邀合作伙伴。
青島非銀機構加力向“新”行
- □青島日報/觀海新聞記者傅軍非銀金融領域作為金融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近年來備受關注,它涵蓋了眾多與銀行傳統業務不同的金融服務機構,...[詳細]
- 青島日報 2025-06-17
煙臺站前現“最窄人行道”
- 本報訊近日,有市民向“煙臺民意通”熱線6601234反映,芝罘區北馬路北側、煙臺站站前廣場的人行道被變電箱截斷,僅容一人側身通行,給市民...[詳細]
- 煙臺晚報 2025-06-17
淄博市企業家看企業暨 “我為企業找訂單”
- 本刊訊6月12日,淄博市企業家看企業暨“我為企業找訂單”——淄川新能源汽車產業鏈供需對接專場活動在山東吉利新能源商用車有限公司雷達汽...[詳細]
- 淄川工作 2025-06-17
區民生建設分線指揮部到淄博師專調研攻堅項目建設情況
- 本刊訊6月12日,區民生建設分線指揮部到淄博師專調研攻堅項目建設情況。區人大常委會主任、區民生建設分線指揮部指揮長周恒學,區人大常委...[詳細]
- 淄川工作 2025-06-17
青島膠東國際機場開啟“雙倍”效率時代
- 本報訊自6月9日零時1分起,青島膠東機場相關平行儀表進近模式實施試驗運行,標志著青島膠東機場跑道運行模式由“兩起一落”優化至“兩起兩...[詳細]
- 金膠州 2025-06-17
國家考古遺址公園,山東+1!
- 記者孫遠明濟南報道近日,第五批國家考古遺址公園評定結果公布,山東泰安大汶口國家考古遺址公園被列入國家考古遺址公園名單。目前,山東已有...[詳細]
- 齊魯晚報 2025-06-17
@中高考生,畢業季免票游山東
- 記者孫遠明濟南報道近日,隨著多地高考的結束,畢業旅行進入熱潮。記者采訪獲悉,全國多家景區推出持準考證免門票政策,旅行社畢業旅行產品預訂...[詳細]
- 齊魯晚報 2025-06-17
夏天就要玩水!6月來濟南開啟“清涼模式”
- 記者張宇寧濟南報道不知不覺,時間已經來到6月,濟南的天氣從春日的溫暖逐漸過渡到了夏日的悶熱。聞名遐邇的“泉城”濟南擁有豐富的河湖、游...[詳細]
- 齊魯晚報 2025-06-17
重要進展!濟南地鐵4號線全線“軌通”
- 季明智濟南報道近日,隨著最后一對鋼軌排在山師東路站左線精準合龍,標志著濟南地鐵4號線工程實現全線“軌通”,為今年年底全線開通奠定了堅實...[詳細]
- 齊魯晚報 2025-06-17
山東各地密集出臺“入境游”政策引客來
- 記者孫遠明濟南報道熱度持續攀升的“入境游”近日,“入境游”頻傳利好消息。6月9日起,中方對沙特、阿曼、科威特、巴林持普通護照人員試行免...[詳細]
- 齊魯晚報 2025-06-17
威海仁川上演中韓自貿“雙城記”
- 2025年是中韓自貿協定簽署十周年。作為黃海兩岸的重要節點城市,中國威海與韓國仁川依托地緣相近、人文相親的獨特優勢,以建設“中韓自貿區地...[詳細]
- 齊魯晚報 2025-06-17
承壓回落!山東雞蛋價格創近5年來新低
- 6月15日,山東省畜牧局發布的最新一期統計數據顯示,全省豬肉價格繼續走低,跌破26元關口,上周豬肉均價為25.99元/公斤,同比降低14.84%,...[詳細]
- 舜網 2025-06-17